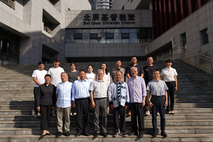我们已经看到“传统”、“理性”及“宗教经验”都对解经具有辅助的作用,那么“普遍启示”又如何呢?
可以肯定的是,“普遍启示”亦能辅助经文的解释,因为“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乃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离开了“普遍启示”,人们很难正确地了解“特殊启示”及其保存——“圣经”。所谓的“普遍启示”就是神向历世历代的世人所作的一般性的启示,一方面神将他自己启示在大自然中,另一方面也启示在世人的心里。也就是说,只要人排除一切的成见与偏见,他们自然能透过宇宙万物及人的良知意识到神的存在、神的伟大及神的智慧。神既然在大自然及人的良知中启示他自己,故此在大自然及人的良知中便留有神作为的痕迹,而最明显的莫过于存在于人的良知中那不可磨灭的宗教意识。在此种宗教意识的驱使下,人类社会出现了宗教与伦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艺术、哲学、科学及各样技能。这些加起来形成了各个时代的特定的历史文化景观。人对“圣经”真理的了解离不开这个特定文化的语境。
一、“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紧密交织
“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乃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因为“特殊启示”乃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场景内,故此人在解释相关经文的时候,时常需要考察经文背后的历史背景,以便使经文的世界能在其历史背景中得以重现。另外,“普遍启示”也出现在“特殊启示”之中,也是“特殊启示”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诗篇”第八篇及十九篇,都提到了神所创造的辽阔宇宙。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便已经将自己启示在日月星辰之中,然而在神的特殊启示及圣灵的默示之下,这些普遍启示亦成了“诗篇”中的特殊启示。另外,我们在福音书中也可以经常看到主耶稣所讲的天国比喻,这些比喻都是透过大自然中最普通的自然现象,比如撒种、生长、收割等情形而成的。这些现象本身只不过是“普遍启示”,但在主耶稣的口中却成了“特殊启示”。
事实上,不仅“圣经”经文内充斥着大量的普遍启示,在我们平时的讲道中,传道人也经常会引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论证神的话语。正如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基督徒的“宗教经验”对于隐藏在经文中的“宗教经验”而言是一种“经验的类比”;同理,“圣经”经文中大量的“普遍启示”也是其“特殊启示”的“类比”,通常,我们将这种类比称之为“存在的类比”。因为“永世”往往是借着“此世”才得以有所领悟的。就如圣礼所显示的那样,我们若有信心,便能借着看得见的礼仪接受那看不见的恩典。
二、人类对普遍启示的回应于圣经诠释的必要性
人类对“普遍启示”的回应形成了特定的历史文化,而特定的历史文化对于“圣经”经文的诠释来说,是必须的。因为文化的基本要素便是语言,而“圣经”经文就是用人类独特的语言文字撰写而成的。神的特殊启示固然超越语言本身,却只能透过有形的语言文字展现出来。
比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作者就将圣子上帝描述成先存的“道”,而“道”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文字,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观念,是中国古代的智者对普遍启示的一种独特认知。和合本圣经的译者将logos翻译成“道”的目的就是为了向活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人们诠释经文原本要传递的真理。当然,我们还可以说logos本身也是一个具体的希腊字以及是一种独特的希腊哲学观念。《约翰福音》的作者用logos来传递真理,也只是将logos视为一种文化载体而已。因为logos本身只是希腊哲学观念中的“宇宙理性”,只是到了《约翰福音》的脉络中,logos才成了“先存的基督”。也就是说“先存的基督”本身超越了logos这个语言记号,却亦是透过logos来表述自己,即那高于它的真理实体。
“圣经”只能透过人类的语言来承载他自己。“圣经”作者用了希伯来语、亚兰语、希腊语等语言陈述那位不可言说的神。与此同时,不同的“圣经”译本,照样使用各国各族的语言文字来翻译“圣经”经卷的手抄本,将“原文”转化成各方各族的人们所熟悉的语言文字。当然,要将“原文”转化至各方各族的语言并非易事,因为翻译的过程其实也是创作的过程,有些经文可以直译,但另有一些则需要意译。如果是意译便意味着翻译圣经的人必须对自己的母语及母语背后的文化相当精通,才能找到恰当的字词来从事译经的工作。
最后,对于讲道或传福音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讲道或传福音的人亦只能使用特定的语言来陈述神的话语。在预备讲章的时候,一般来说,讲道的人应当考察不同的语言文字,比如当他以中文和合本圣经中的某段经文作为讲道经文的时候,他应当考察那段经文的原文以及相应的英文译本,最后再考察不同的中文译本,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查看辞海等中文工具书,以便确定那个中文字词的确切含义。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