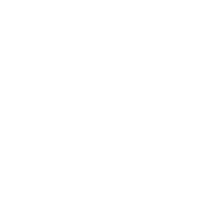在教会历史上,阿明尼乌主义被认为是改革宗中一个观点歧义的主张,它和改革宗正统思想交锋的一个关注点在于预定论。
阿明尼乌主义比较注重的是,上帝有他的预定,藉着耶稣基督的设立的救恩,使人可以得着拯救。它的教义给人一个能动性,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就得着拯救;不接受,就没有办法得着拯救。
改革宗的正统认为,上帝不仅仅是预备了耶稣基督让人得着救恩,而且,上帝以他奇妙的旨意,晓得谁能得救,谁注定不得拯救。所强调的是上帝的主权。阿明尼乌主义比较注重的是上帝有主权,在拯救人这件事上,有他全备的旨意,但这个旨意也是落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愿意跟从耶稣基督,就得着了上帝定意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的拯救,如果弃绝耶稣基督,就不能得着拯救。而按照改革宗正统的观点则是,哪怕那些弃绝耶稣基督的人,上帝如果一定要让他得救,那他也总会回来的。
那么,根据改革宗正统的思想,我们干嘛要传福音呢?有的人注定是要信的,有的人注定是不信的。注定信的人,他一辈子说不信,那最终也会信;注定不信的人,他肯定就是不信。
对于此事,要抱一个敬畏的态度,因为上帝的旨意极其难测。
但阿明尼乌比较开放,就是,上帝是有预备,有藉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救恩,但这个救恩是,愿意了就得着,不愿意的话,上帝也没有办法。
在改革宗的正统里,有五大观点,分别是“无条件的拣选”“有限的救赎”“全然败坏”“不可抗拒的恩典”,“圣徒永恒保守”。其中,“无条件的拣选”指的是,上帝安排谁得救,就是谁得救,从我们人这方面来说,没有任何的善行可以赚得上帝的救恩。这是从上帝主权的角度来讲。马丁·路德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即,我们不能靠着我们的行为,来赚得上帝的救恩。
“有限的救赎”指的是,基督的死是在那些信的人身上,发生它的功效,这也是从上帝主权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全然败坏”指的是,人已经败坏了,所以,在西方神学里,容不得一点伯拉纠主义。所谓的伯拉纠主义,就是人之初,性可能为善。西方的神学观点是,人之初、性本恶,用的是保罗的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东方教会说,世人都有神的形象,因为神把他的形象,赋予了我们,而我们得拯救,是使我们重新有神的形象,至少可以把神的形象彰显出来了。
第四个是“不可抗拒的恩典”,这又是从上帝的主权和威严的角度来说的。
最后一个是“圣徒的永恒保守”,意思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于那些不能得救的,本身就是上帝没有预备他得到神的救恩。
拿教会历史来说,一个强调上帝主权,或者说一个高举基督的人,是不会接受希特勒的。受卡尔·巴特影响很多的潘霍华,就是反对纳粹德国的。因为当时,德国的教会提出一种主张,说希特勒是新德国的救主,就是类似于像弥赛亚一样的人物。但是潘霍华坚持的是“高基督论,从上帝主权的角度,觉得德国教会对于希特勒的尊崇,撺掇了神的主权,所以从心里是厌恶希特勒的。但是,改革宗正统发展到一定地步,人的作为会变得无足轻重。
在改革宗的神学里,有个英文单词,分别代表它五个神学主张的首字母——“Tulip”,就是“郁金香”,因此,一些书里讲到的“郁金香神学”,指的就是“改革宗的神学”。
后来,约翰·卫斯理的神学就是继承了阿明尼乌主义的神学,强调的是,人在上帝的恩典面前,其主观能动性并不是去控制上帝的恩典,也不是去命令神做这做那,而是神赋予我们他的形象的尊严。否则,上帝给我们安一个装置,只要委托我们,都可以根据他的意思去做,那这样的是奴隶,而不是那么荣耀的、替他管理万物的“人”的职分。
另外,冈萨雷斯还讲了“理性主义者”,它来自于对希腊哲学新手法的一种采纳。原来,希腊哲学对于基督教,影响比较大的是柏拉图主义,它主张“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世上的这些事情,都是虚无的荣华,所以,我们应该出离,归到真理中去,其间透露着“出世”的一种倾向。
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主张是,在你能看见的世界上,要去寻找一种认识世界的知识和观念。这应了中世纪,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世界的一个潮流。文艺复兴时期,有大量的艺术作品,描绘的是人的生活和当时世界的百态,原因是人们原来看哥特式教堂,往天上看,后来开始看周边,再看到自己的内心。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心中上帝的概念,慢慢地在减弱。有人开始认为,我要对上帝认识,我需要对周边的世界有所认识,要对我的心有认识,要对自然万物有认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就建立起来了,它的初衷是为了要见证神和多认识神。不过,慢慢地就没了上帝。
理性主义带来的问题,就是“疏离”,就是你原本的想法,和后来发生事情的结果,差距很大。它原来好像是伸出很多眼睛,去观看上帝的作为。但慢慢地,就不是观看上帝,而是观看世界和许多值得去看的、悦人眼目的事情。这样就把上帝放到了一边,他就开始退出了世界的海洋和欧洲主要的舞台。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人起来呼吁,开始注重属灵和敬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