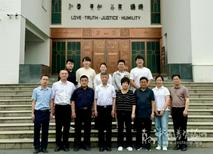《破邪详辩》是清中叶一部影响甚广的反邪教书籍,尤为海外学者所重视,被称为明清以来“唯一无二之专著”。书作的形成源于作者黄育楩的地方治理实践和政治坚守,以及他对白莲教等秘密教门及其经卷的深彻洞察与思考。至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该著作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尤其是作为研究宝卷文学梗概和明清秘密教门的价值不断得以挖掘。然而,对于这部著作可供探讨的政治和社会价值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面对反邪的严峻形势,这部书中所主张的破“邪经”、禁“邪教”等基本观点和实践理路值得认真审视和研究借鉴。着眼当下,应在深化反邪理论研究、促进宣传教育、推进依法治邪和动员社会力量等方面多下功夫。
黄育楩在《破邪详辩》中对邪教及邪教治理的观点
一、“邪教”之“邪”
“不可信也”之“邪心”。白莲教等民间秘密教门在传播时,都会向信众推行一套修持功夫,即“坐功运气、上供升表、考选挂号”,宣扬照此修持即可“达到‘上天’之目的”。这一套修持功夫极具蛊惑性,不仅可以用来稳固信众,还可以用来吸引群众、壮大教门力量。黄育楩长期任职地方,坚守“反邪”一线,深知这一套修持功夫的机理和危害。为此,他除了研究辩驳“邪经”外,还以批判的形式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套修持功夫的虚伪面目,鲜明地指出,所谓修持而“上天”的功夫不过是“痴心”、“谄心”、“妄心”等“坏心”,总体上来说,都是“不可信也”的“邪心”。
“欲借佛教以饰邪教”之“邪经”。《破邪详辩》中所收录的“邪经”,多同于戏文,富有生活气息,通俗易懂、形式多样,并可琅琅上口,这些也正是它能在民间广泛流承的重要原因。而且,从这些“邪经”的内容来看,既有关于仪规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倡导一些道德规范,以及对理想世界的宣扬,其中心思想也主要是诱劝人“安分”。所以,就其内容来讲,“邪经四十余种,并无谋逆之说” 。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佩服黄育楩这样一位长期临民的地方官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敏锐感。恰如他所指出的,“邪经”乃是“欲借佛教以饰邪教也” ,然“邪经为邪教之根源”,若“不将邪经中语,详为辩驳,民既不知邪经之非,虽尽法惩治而陷溺已深,急难挽救。”
“聚众传徙”乃“邪教谋逆”之症结所在。可以说,理清“邪经”-“聚众”-“谋逆”三者之关系是理解《破邪详辩》一书的重点,也是认识作者的治理主张和政治、社会观的关键所在。在《破邪详辩》四刻中,作者都反复强调了“谋逆之原,由于聚众;聚众之原,由于邪经”的观点。黄育楩自己也承认“邪经”本身“无谋逆之说”,或只可“付之一笑”。但他却从更深的层面洞察到,“邪经虽未言谋逆,实为谋逆所自始”。因为“邪经”可以用来吸引群众,“因印造邪经,煽惑愚民,遂致聚众传徙” 。而“聚众”直接威胁到社会稳定,或可成为政局动乱的根源,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最为担心的社会现象。黄育楩敏锐地感觉到,“邪教不可不防,……内地邪教,尤不可不防。直隶拱卫京师,向为邪教渊薮,更不可不防”。他认为,“不复有聚众传徙,又何至于谋为不轨。”
“破邪”绝非一日之功。黄育楩坚持不懈推进“破邪”20年,自然深知“邪教”之顽固,去除之困难。他四刻《破邪详辩》,并在各刻序中反复呼吁地方官员翻印流传。他在《续刻破邪详辩》中提到:“若不续刻《详辩》,恐将来邪教仍复传徙,将以已辩者为邪经,未辩者非邪经。恐初刻《详辩》尚不足以力挽恶风,曲全民命。此详辩之不可不续刻也” 。在《三续破邪详辩序》中,他再次提到:“世之邪民每得一经即借一经以传徙;余故偶得一经必辩一经以防患” 。这表明,黄育楩为“破邪”所做的确实是一种持久战的准备,当然也是一种时刻进行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治邪”之道在于“刑教兼施”、“ 始终不倦”
黄育楩在《破邪详辩》四刻中都反复强调且不断用警语来警示地方官员做好“破邪”、“禁教”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于如何治理“邪教”,他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措施。在《又续破邪详辩序》中,他提出:“务期刑教兼施,始终不倦,则邪教根株,不难尽绝矣”。显然,在黄育梗看来,“刑教兼施”是禁“邪教”的重要途径,或可称为“基本方针”,“刑”与“教”二者缺一不可,但重在详辩“邪经”,这是教化之本,是治理“邪教”的基础,同时更应坚持不懈、“始终不倦”。
黄育楩所倡导之“刑”,一是指严刑峻法。严刑峻法一直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法宝,但对于民间教门而言,似乎失去了原有的震慑作用,连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教之不悟,信之愈坚,不惜躯命,无论金钱” 。也有研究表明,清代统治者对民间教门教首和信徒曾施以绞、斩、凌迟等酷刑,但重刑禁治的实际效果并不如意,甚至统治者的严厉镇压,反而成为教首在传教时宣扬和利用的借口:“谓问成活罪能免地狱不能上天,问成绞罪即不挂红上天,问成斩罪即挂红上天,问成凌迟即穿大红袍上天。” 黄育楩认为严刑峻法这种手段还是需要的,但它仅是“治标之法”,不能成为治理“邪教”的根本方法。他在《续刻破邪详辩序》中非常明确地讲道:“凡遇邪教犯罪,枷杖徙流,绞斩凌迟”,然而“法虽极严,习终难变”,不能触及根本。二是指清查保甲。黄育楩在《破邪详辩》的首刻中即详细记载了清查保甲的方法,他认为“严禁邪教,莫善于保甲”。在他看来,“清查保甲”是一种重要的预防手段,“其法于禁邪为尤要,此《详辩》之首重保甲也” 。
黄育楩所倡导之“教”,重在详辩“邪经”,以为广大民众“启愚开悟”。 他认为,详辩“邪经”,并通过各种方式使之在民间得以广泛传播,渗透至民众日常生活,如此,“在不习邪教者,即深知其非而不为所惑;在习邪教者,亦自觉可丑而逐渐生其改悔之机”。这种做法,确实也得到了清代统治者和各级地方官员的认同和呼应。当然,黄育楩所倡导之“教”,也包括兴办学校以行正面教化 。
《破邪详辩》以及其中的“破邪”、“禁邪”之道对于当下邪教治理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明清以来,民间秘密宗教长盛不衰、活动频繁、扰乱政纲,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等密切相关,尤其与当时的宗教文化政策相关。与今日“邪教”作为一个社会法律概念不同,在中国封建社会,“邪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且封建统治者视民间秘密教门为“邪教”而加以严厉打击的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因此,对于被统治者视为“邪教”的白莲教等民间秘密教门,如何界定其“邪教”性质,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讨论。尽管如此,我们也应看到,像黄育楩这样一位既亲民又长期任职于地方的官员,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洞察社会动乱之症结,并深思熟虑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又身体力行关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基于他的理论思考和地方治理实践而形成的《破邪详辩》以及其中的“破邪”、“禁邪”之道,对于当下推进我国的邪教治理工作,无疑也是有其借鉴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邪教问题的认识和治理工作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完善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初至改革开放初期,以“反革命活动”为名的惩治取缔阶段;二是改革开放以来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依法反邪教的专项行动阶段;三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反邪教工作逐步纳入了法制化轨道的综合治理阶段。历经这个过程,我们明确了“依法打击极少数,团结教育大多数”的根本方针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突出思想教育,重在治本”的指导思想,将教育转化作为对邪教实施综合治理的思想基础和最根本的着眼点。
观照当下,邪教势力依然顽固,邪教孳生蔓延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防范和彻底铲除邪教必定是一场长期艰苦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应当重视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以进一步贯彻落实好我们确定的反邪教工作方针和指导思想。比如:(1)从深化反邪理论研究、促进宣传教育的角度来看,当前还应加强对邪教的特征、群体、组织形式、传播方式、规律,以及历史演变、变化动向等方面的考察和分析研究,并以各种有效的宣传方式,及时向公众公布研究成果,进一步揭露批判邪教的虚伪性、欺骗性、邪恶性及其害人的方法,引导教育信教群众增强识别力、免疫力和抵制力,营造起全社会抵制邪教的浓厚氛围,同时净化正常宗教信仰的舆论空间和社会环境。(2)从推进依法治邪的角度来看,当下,我国反邪教立法还未取得根本突破,打击邪教犯罪的执法和司法还存诸多障碍。应学习借鉴古今中外反邪教立法的经验,适时制定出台符合我国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相关系统性法律。(3)从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角度看,我们更应注重把治理邪教传播渗透的理念融入社会组织常规运行和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促进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4)从加强正统宗教自身建设的角度看,各宗教团体应当在“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这一方针下,对正统宗教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加强对信众信仰素质的培养和训练,积极为社会发展和稳定贡献力量。
(作者系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