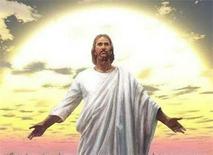先知阿摩司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犹大境内一个名叫提哥亚的小镇上。他靠放牧与修剪树木为生。阿摩司的预言,并非出自正统教育、宗教门第或祭司世袭,而是出自他作为一个农民的视角。
阿摩司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摩 7:14–15)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阿摩司一开始甚至不愿自称“先知”。按理说,他的同辈大可以把他当成一个无知的批评者,但事实并非如此。阿摩司反而成了以色列极具影响力的声音,虽然他几乎把矛头对准了整个民族。学者普遍认为,他开创了“书写先知”的先例,为后来的先知指明了方向,也让他们有勇气公开批评自己的社会。
神呼召阿摩司的时候,正值耶罗波安二世(公元前786–746年)在位,那是以色列国疆域最广、经济最繁荣的时代。许多人以为这是神特殊恩宠的标志,但阿摩司却看见了繁荣背后的腐败。他斥责百姓的罪行、安逸、对军事力量的依赖、社会的不公、道德的堕落与信仰的空洞。他尤其愤怒地批评那些靠压榨穷人过奢华生活的人:“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珊母牛的啊, 当听我的话! 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摩4:1)
这样的直言自然触怒了宗教领袖。阿摩司被逐出王家的圣所,并被禁止在那里说预言。但他没有退缩,回到犹大,把自己公开宣讲的要旨写了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阿摩司书》。
倾向于从上到下
这种“自下而上”的先知传统,在此后的三千年历史中几乎无人重视。我们的社会与教会,总是倾向于从上到下:我们喜欢君王与主教,却几乎忽略了平信徒、妇女和牧人。平民百姓长期被视为微不足道的人,尽管耶稣反复教导我们要关注“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这恰恰反映出希伯来先知精神在宗教史,尤其在基督信仰中所受到的忽视。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有句名言:“文化能把战略当早餐吃掉。”套用他的话:“文化能把宗教当午餐吃掉。”意思是,我们的信念往往更多受生活方式与文化环境的塑造,而非宗教信条本身所决定。不难发现,在许多国家,真正主导人心的往往是文化,而不是信仰。
以罗马天主教会为例,它或许在地理上“普世”,但在气质上却更“罗马”,更地方化。不同地区的天主教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道德观:在英语国家,艺术家往往对裸体羞涩避谈;而在德国与意大利,这却是一种自然的表达。英美的天主教徒普遍重视律法,尤其是教会法;但在意大利人看来,那不过是一个参考意见。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天主教大学中,“约会文化”的盛行程度,恐怕与常春藤名校并无二致。
若一个真理无法触动人心,它几乎算不上真理。真理具有普遍性与绝对性,但它必须在具体的情境中显现。比如,阿摩司依次点名了大马士革、迦萨、推罗、以东、亚扪与摩押的“罪状”——“三番四次的罪”(摩1:3–2:3)。虽然经文并未详细说明这些罪行的内容,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听众对这些罪恶一定了然于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市都是以色列和犹大的邻国,也就是说,这里谈的并非犹太的“约”,而更接近于普世的人性伦理——忠诚与怜悯。真正的先知,会在邪恶滋生之处直呼其名。
让怒火化为新的创造力
阿摩司这位先知,并不只是停留在愤怒与审判之中。他让怒火转化成了新的创造力。在接连发出警告与责备之后,他的语调开始转变。在第四章,他带着一种哀伤的劝诫,重复说了五次:“你们仍不归向我。”这句话里,藏着神的怜悯。
那一刻,阿摩司不再只是愤怒,而是失望。而在失望之中,他竟迸发出赞美:“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这位原本修剪树木、牧养羊群的普通人,在我们眼前成长为一位充满敬畏的诗人。他的愤怒,被炼成了灵性的光。
从阿摩司身上,我们学到一个重要功课:他的预言针对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即使他点名批评圣殿祭司亚玛谢与国王耶罗波安,他们代表的也是整个祭司阶层与统治集团。阿摩司所指向的审判,是面向整个社会、文化与群体结构的。
他深深明白,人们总喜欢把问题归咎于少数“坏人”。但真正造成巨大伤害的,往往是制度与文化本身——贫穷、战争、生态破坏,都源于此。信仰若要真实,就必须面对这种“集体之恶”。如果我们只想着找出几个“害群之马”来定罪,一切都不会真正改变。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耶稣在医治个人的同时,也揭露让他们需要被医治的体制。如果你只把那些医治故事看作“神迹奇事”,可能只会惊叹一句“真奇妙”。但当你追问“为什么这个人需要医治”,你就会看到另一个层面,真正需要被医治的,其实是那整个权力结构,是那些被制度化到几乎看不见的“结构性罪”。
阿摩司责备、批评、警告、应许的对象,几乎全是“集体”。他列出的名单极长:迦密、大马士革、亚兰、迦萨、推罗、以东、摩押、犹大、埃及、亚述、撒玛利亚……他的预言不限于以色列,也包括周边列国。在他看来,所有民族都在耶和华的主权之下。这种普世视野,在今天依然重要,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所体现的,公义不应有边界。
这种“聚焦群体”的先知视角,彻底改变了我们的道德重心。如果我们不承认罪首先存在于群体与结构之中,就会不断去寻找、谴责少数“坏人”,以为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但讽刺的是,我们常常一面谴责个人的罪,一面在制度层面纵容甚至崇拜同样的恶。
看看我们这个世界的矛盾吧:杀人是错的,但战争被看作光荣;贪婪是罪,但资本积累被奉为理想;骄傲是恶,但民族主义被赞为美德;情欲是罪,但调情与诱惑被视为迷人;对邻舍发怒不对,但愤怒的人往往能得逞;懒惰是罪,但有钱人可以尽情享受。
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人感到我们正活在一种彻底矛盾的道德体系下。连“七宗罪”中的贪婪与野心,如今都不再被视为罪,反而被当作美德来推崇。而先知们看待邪恶的角度完全不同。当阿摩司责备“巴珊的母牛”时,他指的不是某个奢华享乐的妇人,而是整个压迫贫民的上层体系。先知们远超他们的时代,他们明白,真正毁灭文明与人性的,是“社会性的罪”:气候危机、战争、巨富神话、名人崇拜、对名利的狂热追逐、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对“共同真理”的否认……这些,才是最深的恶。阿摩司让我们看见,信仰不只是私人的慰藉,而是公共的呼唤,是唤醒整个群体,看见那条通往公义与医治的道路。
为“公共的善”负起责任
在圣经的先知中,阿摩司常常被忽略。他的信息直指权力核心,批评圣殿祭司、反对奢华的王权,却为底层人和公义发声。但今天,我们不太常听到有人讲阿摩司,可能是因为他的话,和我们这个推崇个人主义、习惯把信仰局限在私人领域的时代,实在格格不入。
不妨听听这些话,像不像今天在讲台上会听见的:“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摩2:6)“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摩3:9–10)“我厌恶你们的节期……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5:21–24)
这些话语让人震撼,也让人清醒,原来上帝眼中真正的敬拜,不是华丽的仪式,而是社会中的公平与公义。我们常常把“公义”窄化为惩罚坏人,好像只要把几个罪犯送进监狱,社会就公平了。我们不太敢去面对整个体制里的不公,也不愿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参与其中。我们害怕同时背负“罪责”与“责任”。
但阿摩司提醒我们:真正的道德使命,是为“公共的善”负起责任。这不是要让谁感到羞耻,而是邀请整个社会,一起看见一个更美的愿景。有意思的是,耶稣在谈到末世的时候,也常常用“婚宴”作比喻,不是强调惩罚,而是指向欢庆与和好。
那么,阿摩司所看见的积极异象,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读到他书卷的结尾,会发现那里没有愤怒的咒诅,而是满溢着希望与安慰:“日子将到, 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 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 大山要滴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 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 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 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 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摩9:13–15)
这是多么贴近土地、贴近生活的祝福。是牧羊人和农人能懂的喜乐。它告诉我们:上帝的救恩不是要我们逃离世界,而是要修复这世界,让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在全书结尾,阿摩司更指向一位满有怜悯的上帝:“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摩9:11)
从这里开始,阿摩司开启了一场思想的革命:上帝的心意,不再只是报应与惩罚,而是“复原”与“医治”。祂的爱,是要把人重新寻回,把破碎的修复完整。这个“复和之约”的异象,后来被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继续传递,最终在耶稣的生命中完全呈现。这一完全的呈现,改变了一切,使上帝对受造物的更新与医治成为可能。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安徽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