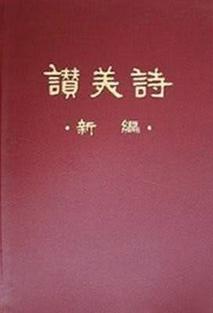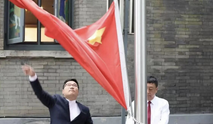在中国教会的发展历程中,圣乐不仅是敬拜的重要部分,也是教会见证与文化表达的独特方式。孙志蓬弟兄多年来致力于圣乐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写作,编写了《赞美诗(新编)词句浅释》《赞美诗(新编)简介》及《赞美诗(新编)补充本史话资料》,同时通过网络平台并著书分享信仰心得与读经体会。本文将走近他在圣乐与文字服侍上的历程与思考。
福音时报:是什么契机、心愿、或者呼召,让您开始编写三本圣乐相关的资料书籍?能够谈谈其中的经历和挑战吗?
孙弟兄:《赞美诗(新编)》是以城市中等文化水平的信徒为对象编写的,灵意和选材,均有独到之处。在用词方面精炼简洁,确非一般信徒所能完全领悟。因此移用于农村教会时,就有不少难懂的词句,若不加以注释,在歌唱时,许多农村信徒往往仅识其文,不谙其义,减少了诗歌原有的属灵价值。我出身在农村,觉得有必要将诗歌中较深的词句加以解释,使大家歌唱时,能达到“口唱心和”的意愿(效果)。
我逐查考《新编》,把诗歌里难懂的字词、倒装句以及圣经典故逐一注释。例如,“死亡已胜过”其实是“已胜过死亡”的倒装句;“银链将要折断”源自《传道书》,指人死后的脊柱松散;“膏油满衣襟”出自《诗篇》;“一同背轭头”来自《马太福音》。一些冷僻词如“纶音”“绵蛮”“卿云”,也尽量加以解释,汇集而成《赞美诗(新编)词句浅释》。虽然因文化水平有限,难免有不足,但希望能帮助弟兄姐妹在唱诗时理解其中属灵意义。
至于编写《赞美诗(新编)简介》,其实在担任诗班指挥期间,我一直都想整理出一本圣诗简介,以供诗班成员练唱时加深理解圣诗的意义,但因资料不足而搁置。同时,全国各教会的诗歌集种类繁多,到底按哪一种诗本编写,我心中没有主见,也就不了了之(因为当时还没有权威的诗集)。
1983年,《赞美诗(新编)》正式出版,让我重拾负担。从那时起,我留心国内教会发行的刊物上有关圣诗的资料,将其一一登记造册,编辑了供自己使用的《圣诗人名歌名词典》,为后续工作打下了基础。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比如人名等译文不统一,我因不懂外文常感无从下手,直到1985年《赞美诗(新编)》线谱本出版,为我解决了这方面的难题。
编写时,我主要参考王神荫主教在《天风》《教材》上发表的“圣诗简介”、“圣诗作者和圣诗故事”,其次取材《天风》作者“灿音”所撰“创作圣诗背景介绍”,以及姜建邦的《圣诗史话》、刘福群《圣诗漫谈》、纪哲生《圣诞歌史话》等,其中又以王神荫主教和灿音所著资料为主,其他为辅。
整理400首诗歌的资料,既零散又繁杂,我必须极目所有圣诗相关的资料,不能遗漏一点,称的上耗费心血,穷思苦索而成。我是一个农村青年,充其量上过初中一年级,小伙子(指上世纪80年代,时年30岁出头)要干“大事”,确实力不从心,难免有人说我好高骛远。但倚靠上主,终于在1988年底完成初稿。
编写《赞美诗(新编)补充本史话资料》的直接原因是2009年《赞美诗(新编)补充本》的问世,我开始搜集相关内容,逐渐积累不少资料。
从2019年3月5日至2020年12月28日,我陆续将搜集整理编写的信息以“赞美诗史话”的系列主题文章在《福音时报》上发表,近两年时间刊出119篇,并尽量按照教会周年节期供稿,与节期等有关的文章共63篇,占全部投稿52.9%。可惜因环境原因,现无法再发表。
2019年9月,我参加了单渭祥牧师(时任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召集的全国两会编写《赞美诗(新编)补充本史话》的筹备会议,参与者还有华东神学院圣乐老师周永慈牧师及全国两会的李清妍姊妹等。我当即提交已经搜集到的《赞美诗(新编)补充本》中123首诗歌的史话资料,作为参考。
此后,我不断更新、补充,2023年2月完成140首,至2025年6月“补充本”史话资料全部完成。期间,罗黎光牧师(原中国基督教圣乐事工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基督教协会会长)、沈光玮牧师(原中国基督教圣乐事工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等前辈一直给予代祷和鼓励。尤其是罗牧师,一直恳切地为我所作的这个事工代祷。每当我遇到写作难处时,我都第一时间向他讨教,请他为我祷告,他都欣然答应。这是我一直不懈写下去的动力。
2025年5月30日,看到基督教全国两会传媒事工部“关于征集《赞美诗(新编)补充本》相关资料的通知”,我心潮澎湃,立即将《赞美诗(新编)补充本》史话资料奉上,当作初熟的果子献给上主,掰开让主使用。
三本书的诞生,前后横跨40余年,既有农村信徒的亲身感受,也有对圣诗传统的执着守望,更有一份“补上空缺、为教会存留”的责任心。虽然个人学识有限,但一路上主赐下异象、开路并加添力量,让我完成了这一段服侍。
福音时报:在中国,不同教会在不同时间、地域、传统内曾使用不同的赞美诗歌本,您觉得《赞美诗(新编)》有何特色?这本赞美诗对当代中国教会的敬拜与信仰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孙弟兄:《赞美诗(新编)》是全国各教会通用的诗集,也是中国基督教两会精心合作而来的文献。照“新编”的序言说,是从各教派习用的赞美诗集中精选汇集而成,其中不少是从国外教会的诗集中选择出来的。它的内容满足了信徒信仰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本崭新而丰富的诗集。其影响深远,是国内教会任何诗集不可比拟、也是不可替代的。
福音时报:你怎么理解基督教圣乐中国化?有没有什么典型人物或者诗歌可以代表您对这个主题的理解?在基督教圣乐中国化的议题下,您认为中国教会圣诗、圣乐的发展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孙弟兄:“本色化”或“中国化”并不排外,并非意味着我们教会脱离历史的、普世的教会传统,并非要我们不唱国外的圣诗。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圣诗、圣乐中国化”在更大意义上,是鼓励、推动圣诗创作的繁荣,圣诗创作要走中国化的道路。我们基层教会,很自然地都喜欢唱中国风味的圣诗。
圣诗、圣乐中国化,首先是对歌词的要求。原则上,歌词必须是一首优美的诗词,而不是散文或其它文本体裁,不过现在都放宽了,不强调这些了……
而且我认为,歌词与诗词也不尽相同,歌词要配合音乐,现代诗词则不需要考虑音乐因素。歌词有三种类型:口号式、直述式、深情式。“口号式”已被社会淘汰,但现今教会里面藉着歌曲喊口号的情况还存在。这些重复地叫喊简单口号的诗歌,不能表达真实心愿,特别是基督教歌曲。我们都要作实实在在的人,不能虚情假意,不要做作表态,不能粗制乱造。相比“口号”,我们更欢迎直述式的歌词——用直接简单的语言来陈述的歌词,多是阐明真理、真道教义的圣诗,表达清楚、精准。深情式的歌词,既是对圣经真理的述说,又有作者的属灵感受,多用含蓄、精炼、意深、情切、优美、有跳跃性的诗的语言。
赞美诗的曲调旋律也可以中国化。中国圣乐要有中国味,使用属于中国文化的音乐语言。五声调式是由宫、商、角、徵、羽(唱名12356)五个音构成的调式,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和民间音乐中,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民族调式的种种变化和音乐理论体系,被称为“中国调式”,这有别于西方音乐的大、小调。汉语是有声调的,乐曲要把语调准确地呈现出来。作曲者要把有中国风味、风格的旋律特点融化在头脑里,从内心唱出曲调,创造融汇中国调式的韵味。
词曲搭配也至关重要。音乐的风格、风味、韵味,要在听感上清楚表明这是中国歌曲。另外中文歌曲最基本的要求是“字正腔圆”,因此曲调要注意配搭、符合歌词的四声音调,不要因曲调原因,改变字的四声;也不要把一个词组分开,音乐走势要与歌词一致。一首歌曲是用音乐来述说这段歌词的内容和情感。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最主要的不同是词曲的配搭。外文歌词的格律、腔调与中文完全不同。如果把外文歌曲的歌词直接译成中文,唱出来就像老外说中文,语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