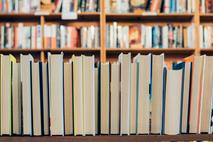一位学者说:“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的传播者和中国革命的参与者。”此话有道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个叫做文华书院的学校,作为武汉唯一的一所教会大学,向武汉介绍了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和科学文化,同时,由于书院所在差会拥有一批倾向于革命的特殊基督徒群体,文华书院也成为辛亥革命的间接参与者,为革命思想的准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华书院,始建于1871年,由美国圣公会在湖北武昌创办,最初是一所男童寄宿教会学校,旨在培养华人传教人员。文华书院最初规模较小,仅有5名学生。为了吸引更多学生,学校不收取学费和住宿费,并提供每日6个铜钱的津贴。1872年,学校迁至武昌昙华林,1873年正式命名为文华书院。
为了适应教育,接着书院进行了教育改革。
1890年,文华书院开始按照西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设立道学、经学、西学、格致等课程,并引入寒暑假制度、班级制和计分制等现代教育模式。
随着发展,1903年,文华书院设立大学部,1909年正式升格为文华大学,成为武汉地区最早的综合性大学之一。1924年,文华大学与英国循道会的博文书院及汉口的博学书院联合组成华中大学。1951年,华中大学被改组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被撤销,部分院系并入华中高等师范学校(今华中师范大学)。
对于文化书院,在华中师范大学的官方网站上是这样介绍的:悠悠岁月,赫赫史册。华中师范大学已经走过了110多年的历史,抚今思昔,追根溯源,奋进在新时期的前沿,华中师范大学倍加珍视自己的历史传承。
华中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一所重点综合性高等学府。追溯其根由,她以1871年的文华书院为源头,以1903年文华书院所设立的大学部为起点,以1924年在文华大学基础上建立的华中大学为主体,以华中大学、中华大学、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等多元结合为前身。1951年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组建成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中华大学、湖北教育学院等并入后,学校改名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年定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学校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并由中原大学创始人之一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
笔者曾经到过位于湖北中医药大学昙华林校区参观,部分建筑仍保存完好,成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和近代教育及建筑历史的重要见证。
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旨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而文华书院与辛亥革命有着重要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教育理念的传播:文华书院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引入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这对当时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产生了冲击。这种新式教育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人才,为辛亥革命的思想启蒙提供了支持。比如:沈祖荣:1905年毕业于文华书院,是中国历史上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的第一人,历任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图书馆主任,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等职;张舜徽:1950年起任教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韦卓民:1903年就读于武昌文华书院备馆(中学部),1907年升入文华书院正馆学习,1911年1月获武昌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前身)学士学位,1915年获武昌文华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著名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宗教学家等。
人才培养:文华书院培养的学生中,有一些人后来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他们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比如:余日章:中国民主革命家,曾任中国青年会会长、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宋教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初期的重要政治人物,被誉为“中国宪政之父”;李公朴: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民主战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斗争,这些人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社会影响:文华书院的存在和发展,对当地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不仅提高了当地民众的文化素质,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开放。这种社会氛围有利于辛亥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接受。
地理位置的优势:文华书院位于武昌,而武昌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之一。这种地理位置的接近性,使得文华书院的师生更容易接触到革命思想,也更容易参与到革命活动中。
由于文华书院是教会学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相对隐蔽性,为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活动空间,使其能够在这里秘密地策划和组织革命活动,避免了清政府的直接打击。
文华书院的校歌有这样一句歌词“为上帝、教会、祖国尽忠争光”,可见师生把爱国、爱上帝、爱教三者结合起来,这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基督教中国化、爱国爱教、荣神益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文华书院作为教会学校十分注重英文教育,学生能够率先涉猎西方书籍,了解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华盛顿、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成为学生熟悉的人物。
但是书院由于不重视国文教育,学生国文水平很差,遣词造句困难。在文华中学校长余日章和胡兰亭的建议下,刘静庵、张纯一、范焕文等日知会会员被聘为书院国文教习。刘静庵课堂上显现出“两眼半开半合,严肃地讲解庄子、墨子诸书,毫不涉及其他问题尤其不谈时务,不讲政治”。但课下及业余时间,他们经常与学生谈论革命反清,“革命空气弥漫学校”。受其影响,一些学生经常参加日知会活动。
1905年,胡兰亭利用自己会长及文华监学的身份在文华书院组织“救世军”、取“耶稣救世”之意,实寓“救国出苦难”。每逢周末,由文华书院学生组成的“救世军”扛着红底黑字的“救世军”军旗,吹号打鼓,到黄鹤楼、阅马场、平湖门一带向市民“布道”,实则宣扬反清,“语多讽刺清廷”。救世军的活动在市民中影响颇大,听者为之动容。余日章在文华教书时,兼主持学生的军操课,使用木制的步枪进行操练。
在当时文华学生军歌特别著名,歌词如下:
“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按剑摩,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从军乐,乐如何;从军乐,乐如何,怎能够坐视国步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对天演烈风潮,争优胜武士道,竞上舞台高,精神好,为国民重新铸个头脑,挣得神州天小,纪念碑立云表。操操操,休草草!操操操,休草草,为国民重新铸个头脑,挣得神州天小,纪念碑立云表。齐昂昂整顿了好身手,讲兵韬。救国千钩担一肩挑,新中国能够造得坚牢, 便是绝代人豪,浩然气薄云霄,声价儿比天高,声价儿比天高。新中国能够造得坚牢,便是绝代人涨,浩然气薄云霄。”
军歌原为文华学生的军操课所用,由于歌词“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与“驱除鞋虏”的反清革命之意契合,在被“救世军”传唱到校外后,在军学界广为流传。武昌首义时,新军在“准备指日探戈,好收拾旧山河”的激励下与清军浴血奋战。
1906年3月,文华书院创办教会刊物《文华学界》,主编由余日章担任,刘静庵、韦卓民等编撰。韦卓民,文华书院备馆(中学部)学生、由于学业优异参与编撰《文华学界》,常以“法兰西士”为笔名发表文章。《文华学界》“为吾国学生定期之先声”,日知会常假该刊发表文意,宣传反清,“文字中隐有革命宣传意,编者用‘新中国之新国民’、‘先觉者’‘法兰西士’等笔名"。学生的行为得到西方传教士的默许、支持、《文华学界》和“救世军”的活动引起了官府的注意,书院英籍监督对办刊的学生说:“有学校保护你们,只要小心你们的行李有没有藏着宣传革命的书籍。《文华学界》是我们学校的刊物,与政治无关。”学生因而有待无恐,常以革命为谈资。
文华书院培养了许多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人才,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启蒙和人才支持。文华书院的教育理念和氛围对学生的革命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文华书院的教师和学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刘静庵、余日章、周苍柏、张纯一、卢春荣等。
辛亥革命中,文华书院的学生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为革命的爆发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下是文华书院学生参与辛亥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
思想宣传方面。文华书院的师生创办了进步刊物《文华学界》,刊发的文章常隐含革命宣传之意,学生们常以革命为谈资,学校充满了自由民主的气氛。这些刊物传播了革命思想,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在组织活动方面,文华书院的教师余日章在校内指导学生创办刊物,并组织学生军。学生军的成立为革命培养了军事力量,提高了学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
更有学生直接参与战斗,一些文华书院的学生直接参加了战斗。例如,董楚臣经黄吉亭牧师介绍任黄兴传令官,参加刘家庙战斗负伤;曹道兴参加汉口之役,其妻傅翠云也加入学生队,因作战勇敢,被称为女将军。
医疗救护方面,在武昌首义中,文华书院的学生和教牧人员组织基督徒参加救护工作,建立临时战地医院,为伤员提供医疗救助。被中国基督教两会编入爱国主义教材的基督徒女医生张竹君在救援中表示“尽我天职,其他均非所计”,展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
文华书院的学生通过这些方式积极参与辛亥革命,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行动体现了文华书院自由民主的教育氛围和学生的爱国情怀。
总之,作为基督教创办的文华书院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通过教育传播新思想,培养革命人才,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