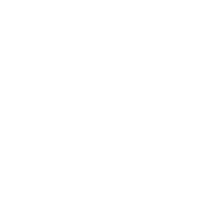在宣教学的课堂上,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化与文明有什么不同?”美国老师只是说这是一个好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发现所有的福音派课件几乎都是以原始社会为场景:衣不遮体、茹毛饮血的社群,而没有放在一个佛教的、儒家的、伊斯兰的或共产主义的“异教”场景下的叙事。文明被等同于基督教世界,仿佛只有传教士带来的原生文化才叫文明。本文就是对教科书中“传教士是在毁灭文化吗?”(“Do Missionaries Destroy Cultures?”)一文的摘评。(近年一个美籍华裔违法进入原始部落传教、被乱箭刺死的事件曾引发过类似的争议。)
我的一个挣扎是,在多数世界的发展中或文明化(或其他恰当的形容词,比如“现代化”)过程中,传教士扮演的准确角色到底是什么?对于传教士的角色总是存在着争议,尤其是他们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对于这个主题,在中国可以听到两种声音。一种声音是现代性是由传教士引入的,另一种是声音是传教士是殖民主义的急先锋。前一种声音,要注意,引入现代性的传教士经常是被基要派所诟病的,比如流行的宣教学教科书只提戴德生,不提纵横清末文化界的李提摩太。后一种声音有时转化成在本土领袖中对教会本土化的呼吁。这个声音并不是民族主义者所独有的,而是像倪柝声等几乎所有过往教会领袖都提出过的。
本土信徒与传教士的关系非常像经典的中国亲子关系——“如果你不听我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下去。”确实可以找到一些经文支持:“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等等,不过这些语句不应该僵硬地解读。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不仅仅外国传教士面临的挑战,也是本土传教士面临的挑战。比如,对于中国经典的价值,在本土牧者中就有分歧:有些坚持它们已经过时甚至是邪恶的,而有些坚持它们是契合福音的珍宝。
比较遗憾的是,相比于其他传统的宗派比如天主教,福音派-五旬宗传教经验太年轻。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记者批评基要派正在“企图完全毁灭当地文化”,“区别于罗马天主教和主流新教传教群体的相对适应政策”。(463)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传教士差遣最多的国家美国仅仅有两百年历史,而且是个地地道道的殖民国家。而大多数美国传教士是福音派-五旬宗,如果我没有错的话。与此同时,美国是现代最强大的国家,这样在很多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中,有一种想象,就是美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美国是整个世界的模板。这个声音几乎在近现代中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可以听到,包括共产党革命时期,以及当代中国基督徒中。
不同于中国的早期景教(聂斯托利派)或天主教传教士与佛教僧侣或儒生合作、视中国文明为平等甚至高于他们自己的原生文明,而现代传教士经常不需要向中国学习,整体上现代中国是劣于传教士原生文明的。比如,现在居留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很多都没有中文基础或古典基础。相比于早期传教士,现代传教士在一定意义上看起来无知或冷漠。一个事实是中国传统文明一定程度上被西方现代文化摧毁了。怎样定义西方现代文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基督教?我不知道。不过我的立场认同一些思想家,就是,华夏文明还没有成功应对基督教(或现代基督教)的挑战。
那篇文章是基督教基要主义和世俗社会关系的样本。他们彼此都互相无知,而仅仅互相敌视。就像美国总统川普在指控几个专业媒体是假的。我想这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危机,其从一开始就存在,已经被朋霍费尔所批评,不应该在宣教禾场上再现了。“异教的”也是属神的。我想我们应该学习早期传教士的经验,比如中国景教-佛教、天主教-儒家,以及巴格达景教-穆斯林的对话与合作。这并不容易,因为现代基要派习惯于不认同记者引用的陈述:“我们相信上帝已经在现有文化中做工。”(464)
在后殖民时代(或泛殖民时代),应该走出只有基督教世界才叫文明的窠臼。其他宗教或“异教”群体也可以叫文明。而作为“文明体”本身,跟其他“文明体”的包容与对话,这才叫文明。如果两个“文明体”只有冲突、没有对话与包容,这本身就不是文明。
Richardson, Don. “Do Missionaries Destroy Cultures?” In Ralph D. Winter and Steven C. Hawthorne, edited,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A Reader, 3rd edition, 460-468. Pasadena, Californi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99.
(本文首发于“信仰和学术”微信公众号,福音时报蒙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