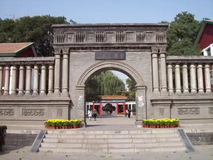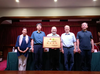编者按:本文节选自《福音与当代中国》杂志第四期文章《晚清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的李提摩太及其传教路线:回顾与前瞻》,由于文章较长,小编想以多篇短文的形式来展现,此处为“对李提摩太和戴德生两种宣教路线的比较:策略”。
1916年5月,李提摩太辞去广学会总干事的职务回国,3年后病逝于伦敦。
李提摩太堪称为“利玛窦第二”,在晚清之际以福音使者的身份游走于中国士大夫之间,甚至参与中国的政治维新和思想变革运动,对中国官员和学者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由于李提摩太诸多卓越表现,清朝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李提摩太和利玛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通过向中国人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来为福音的传播创设条件,比如多多地接触中国的社会上层人士扩大影响力。
但他又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利玛窦。利玛窦来中国只是传布西方科技,而李提摩太来中国正逢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之际,他不仅传播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更传播了西方的政治思想观念,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潮流,起到了强烈的思想启蒙作用。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19世纪末期进行的维新变法就是受到了李提摩太的直接影响。李提摩太是使用上帝的普遍恩典和普遍启示作为打开福音之门的桥梁和手段。
李提摩太作为一位西方宣教士,在时代激荡的19世纪可以说承接了17世纪利玛窦的传统,再次“开启了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会通之门”。
不过,李提摩太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戴德生和内地会的空白,但他的神学观念比较开放,对中国宗教持有过于开放的态度,虽然他尽力想赢得中国士大夫精英的认同和好感,但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弱点,那就是很容易走向混合主义,冲淡基督教福音的根基。
实际上李提摩太的普救论色彩和社会福音倾向在他身后引起了很多争议。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形成了以戴德生和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不同宣教路线,人们对前者褒扬太过,对后者贬斥又太甚。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估一下,而通过这种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深认识李提摩太这位特立独行、别具一格的西方宣教士。
5.1两种不同宣教路线特点的比较
李提摩太和戴德生面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异文化禾场,以不同的宣教方式回应了处境化问题。但就其具体的宣教路线而言,两者则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在宣教对象层面,戴德生注重向普通大众传播福音,走的是平民路线;而李提摩太强调向社会上层人士传播福音,走的是精英路线。
在宣教士资质层面,戴德生看重宣教士的属灵素质要远远高于普通学识,甚至认为不需要神学装备也可以做宣教士,只要有一颗爱灵魂的心就行。但李提摩太却主张宣教士不仅要有一定的属灵素质,更要有相当优良的学术水平。
李提摩太在回国述职的时候写过一本名为《中国急需: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小册子。在这里,就像在其他作品中一样,他仍然强调的第一点是,“对每个新到的传教士来说,除了学习语言外,还应当致力于研究当地人的宗教,研究传教手段,这是基本的、必需的,因为能扩大他们的工作效果。”
在推动宣教事工的实践层面,戴德生非常强调信心和祷告,特别注重直接布道,直接传讲悔改和救恩的福音,快速地抢救灵魂。因此,他不给内地会的宣教士设立固定的薪酬,而是鼓励宣教士们单单仰望神的供应。但李提摩太却主张间接的传福音方法,强调通过向中国人传授自然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破除中国人的无知和迷信,为传播福音开路。因此,他坚持认为,“应当付出跟从事宗教事务同样多的努力去研究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处理的是上帝制定的(自然界)法律。”但戴德生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只会认为那样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与其花费精力去钻研自然科学,倒不如去多多地布道救灵魂。
在宣教的实践果效层面,戴德生着眼于个人的灵魂救恩,扎扎实实地做好一个又一个灵魂的福音和灵命栽培工作;而李提摩太的眼光似乎更远大,强调“全民转变”、“万民归宗”这样的概念,要做广泛的工作。也许李提摩太是受到中世纪时期欧洲很多蛮邦在宣教士的带领下集体归信的历史经验之启示。他曾向英国浸信会提出一整套在要中国实施的教育计划,他希望“所有教会团结起来,在每一个省的首府建一所高级教会学校。首先在沿海各省试办,以便影响帝国的领导阶层,使他们接受基督教。”
为此,他印刷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十五年传教在中国》,在浸信会委员会的成员间散发进行游说,希望能够得到支持,“以期实现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转变”。但这个引领“万民归宗”的宏大宣教计划提案因经费问题而被委员会毙掉。
在宣教的策略和传播手段层面,戴德生基本上采取的传统的布道方法,就算医疗传道也是通常使用的宣教策略,创新性不足。而李提摩太勇于创新,主张并大胆尝试采取新的教育和福音传播手段,比如他深入地推动文字事工和社会关怀。李提摩太主持下的广学会推动出版基督教著作和普及性宗教读物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对中国社会了解认识基督教起到了启蒙和开化作用。
在宣教士的使命层面,戴德生主张宣教士的最大甚至也是唯一的使命就是直接传福音抢救灵魂,宣教士以抢救灵魂为己任,其它方面(比如办医院、建学校)都要服务于传福音的核心目标,而不能本末倒置。可以说,戴德生的宣教是以传福音救灵魂为导向的。但李提摩太却很看重福音使命之外的其他工作,推动中国思想启蒙和文明进步和传福音使命同等重要,不能因传福音而忽略前者。
正是如此,到了20世纪,有人称李提摩太所传的福音很像是“社会福音”,李提摩太被看做是“社会福音派”的代表。
关于这一点,李提摩太的传记作者指出,李提摩太曾发表一次演说,“揭示了传教的重心已经变化的事实。以前的重心在于‘拯救异教徒于地狱的痛苦中’,现在变为‘拯救异教徒于这世界上痛苦的地狱中’”。很明显,李提摩太的神学观念已然具有社会福音的倾向。
在宣教手段层面,戴德生的宣教做的是直接福音工作,注重生根;而李提摩太侧重做的是福音的预备工作,注重广泛,通过介绍西方科技文明、办报纸和出版刊物等来为传福音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观念的引进与传播有利于矫正儒家传统对超自然事物的漠视,扩大了中国人的精神视野,丰富了他们的宗教语言,从而为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在对待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层面,戴德生认同西方宣教士主流看法,就是中国是异教主义,必须从福音中得到解放。“戴氏与其一手创办的中华内地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体系持相当消极的看法。应该说,自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大多数来华新教传士均把中国文明看作所谓‘异教主义’(Heathenism)。在他们眼中,中国文化和宗教中充斥‘迷信’和其它与福音格格不入的东西。用一个内地会传教士的话来说,‘这些非基督宗教背后的无望、无助、堕落、绝望、愚昧、和恐惧极其可怕。’”
但李提摩太却以开放乐观的态度对待中国宗教,并且试图从中国的宗教典籍里找到真理的亮光,并把中国宗教作为走向更高宗教——基督教的一个台阶。当时许多宣教士所写的基督教宣传册子要么攻击偶像崇拜,要么攻击祖先崇拜。但李提摩太认为这些册子在攻击之外连同“把许多中国文化习俗贬低为罪恶,而不承认中国人所崇敬的大多数的事物是值得肯定的。”结果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和中国人的对立越来越严重,“这些小册子所到之处,都会爆发对传教士的暴乱。之所以发生暴乱,不是因为中国人邪恶,而是因为小册子的作者的无知——他们没有全面研究过中国人的观念,却在当地人毫无过错的地方,指责他们有罪。这就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成为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对手。”
因此,他很反感当时一些宣教士对中国宗教尚无充分了解就随便进行指责和论断。他说:“一种宗教,一种赢得了中国最伟大的心灵的信奉的宗教,是不可以等闲置之的。”因此,在李提摩太看来,这种小册子恰恰破坏了它们的作者所要实现的工作目标——因对中国人的宗教文化不甚了解,以偏狭的态度批评中国人的宗教文化,只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最终也无法向中国人很好地传播福音见证福音。
另外,据李提摩太本人称,他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有一个重大发现,“佛教(不是由乔达摩建立的原始佛教,而是指从基督时代开始的佛教)在其高度发展中实际上包涵了基督教的一些主要教条”。甚至他还向和尚们重新解释《金刚经》第六章所提到的预言——书中是这样写的:“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李提摩太把这一段佛教经文解释成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主耶稣基督出现在佛陀逝世后五百年。李提摩太就是这样,总是试图从中国的宗教文化典籍里找到或挖掘出真理的亮光,借此打开传道之门。
在宣教的政教关系层面,戴德生主张政教要分离,只单纯地做福音工作,戴德生基本上不靠本国(英国)政府的强势力量来保护自己在中国的传道事业,一旦遇到麻烦,尽可能先向中国当地政府提出诉求,若得不到中国地方官府支持,他们就宁愿忍受受苦甚至殉道的代价。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内地会数十位宣教士及其家属被杀,但戴德生和内地会却在事后主动放弃索赔事宜。
而李提摩太主张以政促教。1890年5月,第二届西方宣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举办于1877年)。李提摩太应邀为大会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基督传教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论文中,他“呼吁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府,在那些可称为中国的蓝皮书的书籍里,印刷和传播对基督教会的最无耻的诽谤,并且那些出版于二十年前的书籍又推出了更便宜的新版本。”李提摩太由此敏锐地觉察到,一场针对外国人的迫害即将大规模爆发,因而他主张应当立即推举一个委员会,上书皇帝,说明基督徒的真实目的,请求皇帝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教的中伤。此外,李提摩太积极推动宣教士和当地政府官员建立良好关系,他认为这样做能够在宣教士和中国民众之间消除误解和减少摩擦。
虽然李提摩太和戴德生的宣教路线差异很大,但李提摩太的宣教策略还是对内地会和其他差会的宣教士有很大的的启发作用。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内地会一位叫维尔逊的宣教士认识到举办讲座传道的价值,采用了李提摩太的思路和办法,开办讲座吸引群众再布道传福音。在1910-1915年的最后几年里,另一位西方宣教士罗伯逊教授接受基督青年会委托,以更大的规模组织了系列讲座课程,并采用了科学仪器最新资料。此外,李提摩太的这种宣教方式还被推广到其他省份。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无疑地可以发现,李提摩太显然是西方宣教士中的“异类”“另类”,他更侧重通过文化事工来实现福音使命,更侧重上层社会精英,更侧重在政治、传媒、教育、科技、慈善等诸多领域广泛地为福音的传播做预工,并最终达到中国福音化和文化基督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