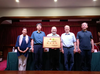近代到登州蓬莱的外国传教士,在这里休假、探亲访友或考察没有定居的不计,子女不计,仅确实有据可查有名有姓在这里生活、居住和工作过的成年男、女,先后就有119人之多。虽然这一统计数字由于有些资料的散失,并不完全,很多人可能没有统计到,但似已能说明近代历史上西方传教士“云集”登州这一现象。
登州府城蓬莱,虽然号称人间仙境,但那时方圆不过数里,人口不过4万左右,1 且地处海边一隅,交通还极为不便,何以会招引如此之多高鼻深目的外国人?这里几乎化为民俗的神仙文化,与西方独一真神崇拜的基督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就本来意义上说,相互抵牾,冲突甚巨;更何况当这些西人东来之时,正值清政府第二次鸦片战争败北、被迫签订屈辱不平等条约之际,中外民族矛盾尖锐。这些陆续前来的外国传教士们为什么能在这种情况下,不唯安然定居,而且得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开创名动寰宇的事业?如果说一开始传教士们只知道蓬莱开港迫不及待而来,后来不久即了解了开港地点换成了烟台,2 为什么还会源源不断地涌进来?
从现已翻阅到的早期来登州和山东的传教士们自己写的保留至今的资料看,虽然在传教士初来的10多年间,一般民众因为“洋鬼子”是在清政府战败后被迫允许他们来的,绅士们由于“洋鬼子”传的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大相抵牾,曾想方设法要把他们赶出去,但当时无论当地政府还是民众,又都清楚中央政府已经和谈立约,自始就给了这些不请自来的“洋鬼子”生活和活动的空间。比如说,美国南部浸信会的海雅西(J. B. Hartwell)1861年初到蓬莱时,经知县允许租赁了城北门附近的一家闲置的当铺;3 是年夏天北长老会的盖利(Rev.Samuel R. Gayley,又作干理、干霖、干雷)夫妇和丹福斯(Rev. J. A. Danforth,又作但福斯、旦福斯、旦富德)夫妇到登州时,蓬莱知县为他们指定了城东门附近的东大寺和寺后的姑子庵作居所,稍后倪维思(John L. Nevius)夫妇来后又租赁了近水门处的观音堂;东大寺及姑子庵后来也一直归长老会使用,不但没有像教会中人所担心的那样,“官指之地,日久年深,官府可以收回” ,4 而且稍后来的梅理士(Charles R. Mills)夫妇虽然困难,但也租到了房子,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夫妇(也是长老会)还买下了毗邻观音堂的空地,建起了崭新的西式住宅和其他一些建筑,观音堂也改造成了学校。5 虽然期间也发生过租房困难,闹出所谓“梅理士教案”,6 但对比第一次鸦片战后近20年间,广州绅民和官府不许外国人根据条约进城,以及福州有传教士租住庙宇被官绅赶走等情形,我们不能不惊叹当时蓬莱官绅民众朴素的理性、正直、仁慈和宽厚胸襟。蓬莱官绅民众在19世纪60-70年代对外来事物的态度,充分显示了蓬莱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应该说,蓬莱文化的这种巨大包容性,是外国传教士能够在这里立足并得以扩展他们事业的根本基础。假如蓬莱也像鸦片战争后的广州和福州那样,在当时尚有浓郁民族仇恨的历史条件下,外国传教士要在这里立足扎根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蓬莱官绅民众所展示的蓬莱文化的理性、正直、仁慈、宽厚和包容,也是胶东文化的特征之一,只不过蓬莱在这方面显得更典型罢了。史载郭显德(Hunter Corbett)、狄考文到中国第一站是在上海登陆,接着他们便和英国浸礼会的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夫妇等人换船直奔烟台。结果船在大约威海至成山一带海面迷失方向搁浅。时值深夜,不仅风大浪高,且阴云密布,漫天飞雪,一众人等弃船涉水上岸,翻山越岭好容易找到了一个村庄。其时天快亮了,大家到一户人家门前敲门。良久,一位老汉开门出来,“老人不懂外国话,众人不懂中国话。彼此手势之下,老者便知就里,又见众人上无风帽,下无棉鞋,衣服尽湿,满身冰雪,即知必是船破得救,前来求助者。初反长毛之后,谁敢照应毛子?乃于此冷意拒绝之时,忽见韦廉臣怀中抱一小孩,此小孩闭眼缩拳,浑身冷战,迨将冻毙,乃大生恻隐之心,放舒冷脸,忽翻笑容,大开其门,招之令众人入”。然后又把家里没起床的人都叫醒到别处去,弄草烧炕,煮饭招待。在得知这伙人要到烟台后,还派人到烟台送信,三天后有英国小炮艇来,才把他们接走。7 这一事实说明,胶东老百姓已经朴素朦胧地把外国侵略者和一般外国人区分开来了。据鸦片战争前到过山东沿海的西方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郭士立(Carl Friedrich Augustus Gutzlaff,又作郭实腊、郭施拉、郭甲利)记述他的亲身经历说:第一次在中国沿海旅行时曾登陆胶州,“发现山东本地人比南方各省居民正直,尽管南方人极其不敬地把他们看成是下等人”。但理性、正直、仁慈、宽厚和包容并不等于柔弱可欺。郭士立第二次中国沿海旅行时在威海卫登陆,经过观察对比,他认为胶东人“如果给以很好的训练,他们会成为优秀的战士”,因为他们是他在各地“见到的所有中国人中最勇敢的”。8
勇敢而不盲目就是理性的表现。外国来华传教士从整体上说,与外国侵略者不是一回事。19世纪来华的西方各国传教士特别是基督新教传教士,与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明确地写进了一些国家的宪法。十分了解中国社会和统治阶级上层关系的英国独立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9 1900年在纽约参加“普世布道大会”(the 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有感于中国维新变法失败顽固守旧势力上台后的严峻形势,认为全体在华传教士有性命之忧,曾建议大会执委会“请求大会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某些措施,以避免危险的灾难。然而,大会执委会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他们认为不应该干预政治”。紧接着,他又通过各种关系,联合其他人计划直接到“华盛顿向政府提出申请,但结果障碍重重,难以逾越”。当时的纽约商会主席杰苏普(Morris K. Jessup)根据常识明确地告诉李提摩太说:“除非发生可怕的大屠杀”,政府绝不会“采取任何行动”。10 政教分离在当时的美国尤为明显。那时的登州百姓,尽管并不了解这些,但他们从自己的政府官员那里知道朝廷与外国立了约,允许这些人来传教,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甚至采取制造一些荒诞的谣传孤立不请自来的“洋鬼子”,可始终没有用盲目的驱逐或伤害方式赶走这些不速之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朴素的理性思维在起作用。
历史已经证明,愚昧盲目的排外心理和行为不能够救中国。虽然我们不能说盲目愚昧的排外行为是不爱国,但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救国,因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11 而要学习别人的长处,首先必须有理性的心态,正确地对待迥异于本地的外来事物。
狄考文传记的作者费舍,是狄考文大学和神学院的同学,后来担任美国汉诺威学院院长,十分关心国外布道事业,两人长期通信。狄考文去世后,他用两年时间阅读了大量狄考文生前的各类信函、文章和自传手稿,写成狄考文传,在谈到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登州所遇到的情形时,说“登州人对外人的态度,似乎确实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甚至直至今天的态度要友好一些”。12 他这里所说的“登州人对外人的态度”,指的是狄考文刚到登州不久当地人对外人的态度,而他所说的“今天”应为写作此书时的1909或1910年,前后相差40年登州与其他“许多地方”对外人态度的比较,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这时清政府已经推行新政改革业近十年,在全国范围内主动学习西方,很多省份都自辟商埠对外开放,山东的济南、潍县、周村,就是1904年由山东巡抚周馥联衔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申请对外开放,经清政府批准辟为商埠的。
中外历史学界的研究已经表明,如果中国能像日本一样早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清末全方位的社会改革如果提前三十年进行,中国近代社会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但可惜的是,中国封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历经庚子一役才幡然醒悟,但却为时已晚。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
除上述根本性原因之外,外国传教士在晚清时期能不断“云集”登州,还有几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其一是当外国传教士登陆蓬莱之时,恰值捻军横扫山东之际。历史上人们愿意把捻军说成是太平军的盟军和友军,是反封建的力量。事实上,早在1861年秋捻军第一次北上山东,即给胶东带来了巨大破坏。这些人根本没有政治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吃饭和财富到处掳掠抢劫。他们“所到处,肆行杀戮,如同蝗虫,类聚群分;如同瘟疫,传染甚速。叩其所为,自己亦茫然不知。至则焚掠屠杀,人烟为虚。骡驴牛马,饥则宰而食之,饱则驱之荒郊,任其飞奔。青年壮丁,则掳之驱赴重役,否则杀之。千军万马,乌合之众,来则如山倒,如潮涌,去则如疾风、飘云,倏忽不见”。当时登州农村,青壮年闻风躲进山林,老弱多在劫难逃,小脚女人更是凄惨备至,很多地方这些小脚女人要投水自尽而不可得,先跳者死了,后来者井已满,于是婴儿遭殃,妇女遭难。登州城里,已人满为患,饮食难继。在这种情况下,新来乍到的外国传教士,经商定派盖利牧师“乘马由海岸间道至烟台求接济”,数日后返回时,因城外捻军未撤,官员拒开城门,不得已用绳拴筐子吊入城内,“众人见此法可以救人,亦以此法试之,救上许多难民”。与此同时,城里的传教士“成立一慈善会,设立临时医院,另立救济院。空手进城者,身得重病者,为贼扎伤者,皆有所救济”。13 这一次捻军在登州造成的灾难,以及随后接踵而至的霍乱大流行,带有西医药物并略懂医道的传教士参与救治病人,把许多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无疑缓和了当地人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甚至消除了一些偏见,打下了最初和平共处的基础。14
其二是19世纪的登州在全国来说,是一难得的避暑和疗养的好去处,当然也是一些不适应南方气候的传教士理想的工作之地。据狄考文传记的作者说,“在那个时代,中国北方的北戴河(Pei-taiho)、南方的牯岭(Kuling)和莫干山(Mokansan)都还没有辟为避暑地。烟台和登州是唯一可以避暑的地方,这两个地方除了传教士们的家,都还没有接待客人的住处。由于美丽的位置,相对清洁的城镇,登州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去处。通常,如果有人向任何一位老传教士提到登州,他都会接着脱口评价说:‘非常讨人喜欢的地方,我曾经在那里同狄考文度过了一个夏天’”。15 早期到登州的传教士,不少都是由于这一原因而从别的地方转来的,像倪维思夫妇,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又作高弟佩、高乐福、高泰培、库劳福)夫妇,梅理士夫妇等,都是因为健康原因从宁波、上海等地北上寻求气候条件适应的所在才来到登州的。至于每年夏天到这里来度假的传教士更是难以尽数。
其三,也可以说是附带三条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即是狄考文在这里相对宽松和谐的中外交往环境中,到登州的第一年,即创办了全包学生衣、食、住、行及医疗和学习用品的寄宿学校,用中文授课,四书五经为学生学习重要内容,教学质量赢得了当地及远近民众的信任。后又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大学,而且“几乎无疑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16 成功教育家的名声在传教士圈内尽人皆知;他花费“十余年之心血”,抽时间“遍游北京、南京、上洋(海)各埠探问访求、实地研究”编纂而成的《官话类编》(即人们平时所说的《官话课本》),17 是当时外人学习汉语的最好的入门书,他本人因此被来华传教士誉为北中国传教士们“学习汉语的一本大书”。18 在狄考文离开登州前,很多传教士都是到这里学习汉语和见习传道的。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外国传教士“云集”登州的原因,与第二次鸦片战后清朝中央政府的政策变化有极大关系。第二次鸦片战后签订的一系列中外约章,规定外国传教士可到内地游历和传教了,还允许法国传教士在内地买地建房(尽管有争议,但不久就基本解决了),这种变化对各级地方官员来说,影响是巨大的。第一次鸦片战后广州人不让外国人根据条约进城,事实上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在背后支持的,他们通过地方士绅挑动下层民众阻止外国人进城,然后借口民众闹事与外国人谈判说不是政府不遵守条约,而是害怕民众闹事,外国人进城不安全,所以要缓一缓再说;福建福州把租住庙宇的传教士赶走,也是官员和士绅们倡导的。近代一些所谓反洋教斗争,跑在前面的是下层民众,最后处理起来倒霉的也多半是下层民众。以往的研究者往往把这样的斗争说成是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殊不知最初信教的才是下层民众,而反教的是政府官员和士绅,他们不出面,在暗地里挑动下层民众闹事,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而且,很多所谓反洋教斗争,根本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反侵略斗争,更多的只是一种文化冲突。今天再回头看那段历史,不能不深长思之,注重实事求是。
谈最后一点,并不能否定各地民风的差别。后来的义和拳之乱,爆发于鲁西南,波及整个北中国,但胶东地区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义和拳,就是明证。历史是复杂的,语言是苍白无力的。想还原历史,太难,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做,尽力而为,就算是对得起过去和明天、先人和后人了。
注释:
1. Alex. Armstrong, Shantung (China) a general outlin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province: a sketch of its missions, and notes of a journey to the tomb of Confucius,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1891,PP.61.
2.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在晚清历史上,西方人似乎一直把登州视为开放口岸,并没有因为烟台开港把登州视为内地,中国政府似乎也一直默认外国人这种认知。其中原委,很可能是由于烟台当时不仅还只是个渔村,而且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建制,是属于福山县辖区的一个贸易口岸,而福山县隶属于登州府。中国内地会就一度在福山县传道。
3. 同上,pp.111-112.
4.连警斋编《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40年版,第160。
5.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1911,PP.76-80.
6. John J. Heeren, On Shantung Front: A History of the shantung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 S. A. 1861-1940 in Its Histo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etting,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ew York, 1940,pp.87-88.
7. 连警斋 前揭书,第32-33。按:胶东农家那时的炕,既是家人晚间睡觉的地方,冬天也用来放上炕桌或“圆盘”吃饭。
8.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p.177-178.
9. 原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后因传教方式与英国浸礼会本部发生矛盾,遂一度脱离浸礼会,靠著述和为报社做编辑等自谋生计传教,曾在建议和鼓动中国变法维新方面不遗余力。
10.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212.
1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59页
12. Daniel W. fisher前揭书,p.71.
13. 连警斋前揭书,第145-146页。
14.Daniel W. Fisher前揭书,1911,p.72
15. Daniel W. Fisher前揭书,P.84.
16.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40.
17.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刊印,第3页。
18.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190.


.jpg?w=213)
.jpg?w=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