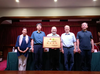狄考文,字东明,一位普通农民的长子,1836年1月9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洲坎伯兰县(Cumberland Co. Pa.)。1864年1月到登州,1904年随登州文会馆迁潍县,1908年,率圣经翻译委员会在烟台审定官话圣经,得腹泻病,初未注意,后拟返回潍县,途中曾赴青岛就医,不治,9月病故,葬于烟台长老会公墓。
有人说狄考文出生于一个小农场主家庭,似乎比较富有。事实上,美国农民不像中国,大都集中于一个村落里,而多是单独一家开辟农场生活。狄考文出生时,虽然父母努力开垦经营,但家境并不好,一家人还只住着“俭朴”的“小木屋”。后经夫妇“勤恳节俭,精打细算”,到狄考文成年时,虽然已经“积累了相当财产”,但还是除了自己劳作外,指望孩子们帮一把,不愿意狄考文兄弟姊妹们离家到外面发展,1 这也是一般农民的惯常思路。不过,狄考文的父亲还是开明的,只要子女能走上成功的道路,他并不坚决反对他们离开家庭。相比较而言,狄考文的母亲更支持孩子们走出去,因为她本人“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上学太少;据说在70岁以后,有一次梦见她被送到霍利约克山(Mount Holyoke)学校读书,醒来流着泪发现自己满头白发,原来这只是一个梦”。因此,尽管狄考文兄弟姊妹7人,“孩子们上学要拖累她付出大量心力和体力,不停奔波操劳,但她要孩子们不断深造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她自己渴望受高等教育,但从未达到目的;孩子们受到了高等教育,她感到极大的满足”。她一生“所设定的各项目标”,除了自己受教育这一项,其他“都很好地实现了,她要求自己做事持之以恒、遇事坚强、富有自我牺牲精神”。2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狄考文从小就经历了艰苦的磨练,成年后多次为继续求学,自己打工、办学挣钱,攒足了钱再求学。狄考文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受家庭影响,大学毕业后决定做一名到国外传道的传教士。为了继续深造,积累传道资本,一度教书为业,“发展顺利,很容易赚到钱”,但他始终觉得上帝在“召唤”他“去传播福音”,于是在母亲的支持下,卖掉了他已经办得很红火的学校,又到神学院读了两年书。神学院读书期间,利用假期义务传教。神学院毕业后,在选择为林肯的北方军队战斗还是践行自己的志向时,义无反顾地奔赴中国。3
狄考文虽然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但却是中国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教育家。他所创办的登州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里所谓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是指包括外国教会、中国政府以及私人创办的大学在内的所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4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是西学东渐的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来华传教士率先在首批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兴办了现代学校。第二鸦片战后的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中开明官僚主持兴办了旨在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先进科技的西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工艺学堂(1868年)、广东实学馆(1876年)、福州电报学堂(1876年)、天津电报学堂(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金陵同文电学馆(1883年)等。但是,普通的中小学教育,除了传教士开办的之外,依然阙如。登州作为第二次鸦片战后的通商口岸之一(后改烟台),自1860年起一些传教士陆续来到这里。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先来一步的美国南部浸信会牧师海雅西夫妇曾经办过学校,但种种原因时办时停,一直没有成功。1861年到登州的美国北长老会牧师倪维思夫人,在1862年冬季创办了一所现代女子学堂,也是时办时停,成效不著,最后几经波折,改为文会女校,才走上正轨。1864年到登州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当年秋天即创办了登州蒙养学堂(登州文会馆前身),虽然早期很艰难,但却不仅坚持下来,而且逐步发展壮大。1877年(农历1876年底),第一批三名十年学习期满,成绩优秀,狄考文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颁发了文凭。毕业典礼的同时,蒙养学堂改名为文会馆,“取以文会友之意”,拟“将天下至要之学会聚于兹”,5 因此,后来齐鲁大学的学生把这首批三名毕业生视为齐鲁大学首批校友。当然,这时的登州文会馆还只有中学程度,或有些课程高于一般中学,但尚不具备真正大学水平。不过,翌年,狄考文即计划要在保留中小学的基础上,把登州文会馆办成大学,并制定了各种规章。1879年,狄考文利用回国休假之机,广泛游说,多方筹款,为办大学做准备。
1881年1月,狄考文回到登州,一边大规模加设大学课程,一边再次向长老会美国差会本部提出办大学的申请。1884年(一说1882年),美国长老会差会本部正式授权登州蒙养学堂办大学。1905年初,登州文会馆迁潍县,合并当时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开办的广德书院(Tsi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中的大学班,更名广文学堂,稍后成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即齐鲁大学的文理科(science and arts department,也称文理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文科、理科。当时医科在济南,神科在青州。1917年,广文学堂和青州的神学院迁济南,是为济南齐鲁大学的文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后来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两个院,神学院独立出去,仍为三个学院)。
由上可见,登州文会馆才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它比号称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992年开始开设大学课程,1906年学校在美国注册,正式称圣约翰大学),即便从1884年算起(其实此前数年已开设大学课程),也早了8年;比号称中国政府办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至少也早11年;6 比号称“最早的国立大学”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筹办,1902年正式开学),要早近20年。
据北京大学教授王忠欣在美国三年研究的结论,登州文会馆在成为大学以后,所开设的西方科学方面的课程,“在当时中国的学校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而社会科学方面的“心理学、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当时称为心灵学、是非学和富国策)”,则“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课程”。7 如上所述,美国学者小海亚特也认为登州文会馆“几乎无疑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8 后来中国政府办大学的情况,以及各省中高等学堂包括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聘用教师的情况,都证明了登州文会馆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既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也是最好的大学。
1898年维新变法高潮期间,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曾授权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字冠西)选任教师,丁韪良就选了8名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担任数、理、化各科教习,一人担任汉文教习。1901年,历经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役,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心实行全面改革,举办新式学堂即是重要内容之一,下令全国“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9 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响应,由于他曾跟随宋庆在登州呆过,熟悉登州文会馆的情况,遂邀请当时文会馆馆长赫士(狄考文1890始出任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馆长即监督一职由赫士接任)到济南负责创办山东大学堂。其时大多数传教士本来已主张在中国多建现代大学,接到邀请后即率领文会馆外籍教师和学生,完全按照登州文会馆的模式、规章,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创办起来,是为响应中央政府指令创办起来的中国第一所省级大学。结果,袁世凯上奏办学情况并拟定章程计划,朝廷当即下令各省“仿照举办,毋许宕延”。10 一时间,文会馆学生供不应求,“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11
作为一名传教士,狄考文早在他确立了到国外传道志向时,就曾坚定地表示:“我决意把我的一生献给中国,住在那里,死在那里,葬在那里”。他实践了自己的志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最后葬在了中国。在四十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晚年他在一封信中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具有辉煌的前途。很高兴我有机会为她迈向辉煌做了我所能做的事情”。12
诚然,狄考文年轻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那是从宗教信仰出发,决心向中国传布上帝之爱,带有浓郁的征服异教的宗教冲动,但也无需否认那时基督新教的海外宣教运动具有强烈的关切民生和人类所有民族进步的属性,尽管这一属性是基于所谓基督救世和上帝之爱。事实上,就狄考文一生来看,与其说其给中国带来了基督福音、上帝之爱,不如说他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
早在1913年,登州《文会馆志》的作者就以亲身经历和体会赞扬狄考文为近代“大著作家”、“大教育家”、 “大制造家”。13 美国现代学者小海亚特则在20世纪70年代称颂狄考文不仅“是首批在中国传授现代西方技艺的人之一”,而且是这首批向中国人传授现代西方技艺的人中“在基督教、科学和汉语方面均有造诣的屈指可数”的人物。认为“如果说他不是个天才,那也是最好的美国式多才多艺的人,一个可说是与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及典型的得过21次奖章的最高级童子军相伯仲的全面成功传奇人物。他一生忙于‘大部分人都难以承受的工作’,在著述和教学方面功勋卓著。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科学家、发明家和家庭工业家”。14 纵观狄考文一生在华业绩,这些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
就教育家、著作家而言,如上所述,狄考文最先为中国完整引进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做出贡献的人才,在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先后担任“中国教育会”、“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15 主持编定现代学校初、高等各科教科书,以及“官话和合译本”圣经的翻译,一生独自或与他人合作编著、译编各种教科书和宗教著述数十部。他主持翻译的《官话和合本圣经》被海内外认为是最规范的白话即现代语言译本,其语言成就,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中国新文学起到了催化和示范的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他率先引进和普及推广了阿拉伯数字,以及“+”、“-”、“×”、“--”(÷的最初写法)等现代国际通用的数学运算符号。中国科举制下的传统教育,数学不受重视,数学学习“都是师徒间个别传授”,19世纪中期以降,数学已落后日本很多。虽然百日维新前后“开始提倡办新法学校”,但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直到1906年使用的数学教科书还是翻译的日本教材,“直排,文言文,没有阿拉伯数字,数学记号仍沿用李善兰所创的那一种”,民国以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到新文化运动期间才“渐有代数学高等教育的雏形”。而狄考文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即已开始在他开办的学校里讲授现代数学了,1877年,更“主持成立了教科书委员会”,计划编写初级和高级两套现代学校教科书,每一套都包括“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他和他的学生邹立文根据登州文会馆教学经验合编的数学教材《形学备旨》(1885年出版)、《代数备旨》(1890年出版)、《笔算数学》(1892年出版),都“采用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这些书“发行很广,每种书都重印了十几次,清末许多学校曾采用作为教科书”。民初在很多地方还有很大影响,如所周知,我国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就是因为少时看到《笔算数学》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走上了攀登数学巅峰之路的。
从制造家、科学家、发明家、家庭工业家称号看,狄考文也当之无愧。王元德、刘玉峰以亲历亲见,说登州文会馆的大部分物理、化学、天文各科实验仪器大多是狄考文仿造的,“精巧坚致不亚泰西之品,除本堂应用外,各省学堂亦争相购定”。民初“山东理化器械所以所制物品陈列南洋劝业会,咸称为全国第一家,其监制者,即先生高足丁君立璜也”。17 狄考文传记的作者费舍则根据当时人郭显德、赫士、狄考文继室夫人等的记述和狄考文本人的日记、通信,说狄考文在1880年代初即在蓬莱城里建了一个“一个相当完善的制作所”,“制作所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用来制作各种仪器或电气及蒸汽设备的器械,以便于他随时可以制作任何器具,从装配一台风车或水利系统,或一台引擎、发电机,到为眼镜框镀上黄铜、修理自行车,什么都能做”。“早在西方尚未普遍制作电铸版之前,他就搞到了一套设备,并教授了一班中国工匠。当电风扇时尚起来以后,他购买了一个小风扇做模型,接着就制作出了另一个”。18
登州文会馆之所以能够成功,狄考文的夫人狄邦就烈(Mrs. Julia A. Mateer,狄考文原配夫人)功不可没。狄考文晚年回顾他们数十年间艰难备尝,从创建一个只有几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的可怜小学堂,到逐步办成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历程时曾说:“在我早年的生活中,上帝对我最大的祝福是邦就烈。她与我共同承载每天的负担和心事,文会馆的成功大部分应归功于她。她的去世是我一生的最大损失”。19
狄考文夫人原名邦就烈(Julia A. Brown),1837年生人,少时失去双亲,14岁偕妹妹寄居舅父家中,18岁开始自谋生计,25岁与狄考文结婚来登州,1898年在登州去世,享年61岁。
她一生在登州传教、办学,没有生育,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登州蒙养学堂、文会女校的学生们。有人说她“像母亲一样照料学生们,到乡村长途旅行访问学生们的母亲和其他妇女,负责饥荒赈济,编写音乐课本帮助学生学习唱歌,劝导和鼓励本地牧师,为持续不断前来的见习传教士安排食宿,照料病人和无助的人。虽然她不是很强健,但她总是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在为别人做事”。20 有关研究显示,她很可能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乐教育引入中国的人。据狄考文在大学和神学院的同学,也是他一生的好朋友,后来担任汉诺威学院(Hanover College)院长的费舍所著《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一书介绍,登州蒙养学堂刚开办时,由于语言不通,先聘请中国老师教学,但不久狄考文夫妇就开始亲自上课,狄考文教算术,狄邦就烈“教授地理,向孩子们介绍中国以外的世界,开阔他们的视野。她每个星期还有三次特别难做的工作要做,那就是教孩子们唱歌”。21 登州蒙养学堂创办伊始就上音乐课,这很可能与狄邦就烈青年时期就做过数年教师有关,这种情况在早期的教会学校中是很少见的。早期教会学校的办学目的,主要是培养宗教人才,虽然有些教会学校也学习唱歌,但尚未发现有像蒙养学堂那样的系统音乐教育,也没有见到比狄邦就烈编写的《乐法启蒙》(1872年初版,1879、1892、1907、1913年曾多次补编重印)更早的西方音乐教材。现代音乐教育,在清末新政改革时期废科举、大力兴办现代学堂的运动中,也还不是必修课,而登州早在1860年代中期就每周三次必修了,早于中国推广现代音乐教育至少40年。这些,已为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者所熟知。
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登州蒙养学堂的音乐教育一直延续到文会馆时期,现存登州《文会馆志》中保留的一些该校校歌,都是文会馆的学生创作的五线谱曲,二、四部合唱歌曲,这说明登州文会馆的音乐教育是相当成功的,可以说独步当时中国音乐界。22
注释:
1.Daniel W. Fisher,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1911P.17-19.
2.Daniel W. Fisher前揭书,p.21.
3.Irwin T. Hyatt, Jr.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pp.140-145.
4. 有人把天主教耶稣会1594年在澳门创设的圣保禄学院与近代中国人和中国政府设立的诸多大学放在一起讨论“谁是中国第一所大学”的问题,实有模糊概念之嫌。首先,圣保禄学院创设于1594年,1762年关闭,是一所欧洲中世纪神学院的移植,虽然该学院也教授历史、地理、哲学以及很多当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另外增加了中西语言课程,但严格讲依然是一所神学院,并没有完成向世俗大学的转化。中西语言教学(主要是拉丁文、日语、中文)的目的更是为传播基督教服务的。其次,说它是西式大学是可以的,但却不是近代西式大学。近代,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概念,一般是指1840——1849年这一历史时期(过去是指1840年——1919年),圣保禄学院早在十八世纪中期就关闭了,那时中国远没有进入近代。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圣保禄学院所教授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严格说,还不能算是近代科学知识。众所周知,虽然世界资本主义从文化思想领域说始于“文艺复兴”时代,但世界范围内进入资本主义也就是近代的科学标志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的,而圣保禄学院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关闭的。因此它所教授的自然科学知识,还不能与“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相提并论。
5. 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刊印:《登郡文会馆典章》,第1页。关于文会馆改名的时间,另说为1876年,实际上不同资料说的都是一个时间,中国近代直至民国年间,很多人记述时间,年用公历,但月份往往仍然用夏历即阴历,这样一来,记述某件事发生的时间,如果在年中,时间就没有大的分歧,而如果是年初或年末只差一个月,往往就差了一年。登州文会馆改名时间按阴历月份,是1876年末学校放寒假之前,按公历即阳历则是1877年年初。后来登州文会馆迁潍县的时间有说是1904年,有说是1905年,也是这个道理。
6.1895年10月光绪皇帝诏准创办“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996年正式创办,更名“北洋大学堂”,义和团运动期间成为八国联军兵营,1902年袁世凯奏请拨地重建,改名天津北洋大学堂。
7. 王忠欣:《传教与教育》,网络版,第三章“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的产生” http://www.hleung.com/CS103/cs103ch2.htm.
8.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140.
9.朱寿朋 编,张静卢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二版,总4719。
10.同上书,第4787页。
11.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刊行,第4、5-6页。
12.Daniel W. Fisher前揭书,第305、319页。
13.王元德、刘玉峰前揭书,第5-6页。
14. Irwin T. Hyatt, Jr.前揭书,p.139.
15. 中国教育会,是外国在华传教士为推广教会学校教育而联合成立的编写和出版学校教科书、宗教宣传著述、各种西方现代科学通用术语工具书等的机构,由狄考文在1877年全国传教士大会上倡议发起,原称“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名称“益智书会”。在1890年第二次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改名为“中国教育会”——“The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中文习惯上仍称“益智书会”。“圣经翻译委员会”是鉴于以前翻译的各种版本的圣经不准确,1890年全国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大会决定组织力量重新翻译而成立的一个机构,狄考文任主席。他主持翻译的圣经,被称为“官话和合本圣经”,白话,被认为是最好的圣经译本。
16.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1卷(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0-1785页。
17.王元德、刘玉峰前揭书,第4、5-6页。
18. Daniel W. Fisher前揭书,pp.239-242.
19.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前揭书,p.192.
20.同上。
21.Daniel W. Fisher前揭书,pp.136-137.
22. 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音乐研究》,2006年第2期。孙继南先生在文中称登州文会馆的正规音乐教育,比近代开风气之先的上海还要早“三十多年”。对《文会馆志》和其中的“文会馆唱歌选抄”所刊载的10首“乐歌”的发现感到震惊,并通过咨询有关专家、进行研究后认为:“理性认知告诉我们,中国‘学堂乐歌’的历史需要‘改写’了”!不过,孙先生在文中“除最后一首《爱国歌》为《馆志》主编刘玉峰于1912年‘民国’成立时为‘适合共和政体’而编写的外”一语,有误。事实上,《爱国歌》并非是编写于1912年,而是早就有,只不过因为原来的歌词中所爱的国不是民国,而是大清国,所以民国建立后,原来的歌词不适合民国新政体、新形势了,于是重新改编了歌词。正所谓 “词另改作,以期适应共和政体”,见《文会馆志》第73页。


(图:贺卫方的博客).jpg?w=900)
1.jpg?w=900)
.jpg?w=900)
(图:贺卫方的博客).jpg?w=172)
1.jpg?w=172)
.jpg?w=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