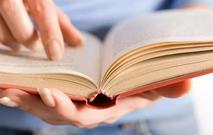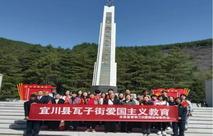一、暗室:光与尘的相遇
尘封的暗室,总孕育着重见天日的光。
比如那支银笛,它静默地蜷伏于圣殿废墟的深处,3000年的光阴如灰烬般覆盖它的音孔,似尘埃般封锁它的呼吸。当考古学家的指尖,带着敬畏,轻轻拂过它冰冷的表面时,一道细微的叹息,如同穿透岁月的裂隙,幽幽渗出——这可是利未人最后一次吹奏时,那未曾散去的颤音?他们曾虔诚地站立在至圣所神圣的幔帐前,用银笛流淌的音符,温柔地编织着祭坛上袅袅升腾的烟雾,将万民的哀恸与祈愿,小心翼翼地揉进献给耶和华的馨香祷告。直到那一天,巴比伦铁骑无情地碾碎象征信仰的廊柱,如同命运扼住了夜莺的喉咙,再也发不出半点声响。
然而3000年后,当学者怀着虔诚,对着那饱经沧桑的裂痕轻轻吹奏时,音符如同蛰伏已久的萤火虫,扑簌簌地挣脱束缚,带着微光,重新飞舞于世间。原来,赞美的旋律从未真正消逝,它只是如同饱满的种子,静静地蜷缩于黑暗之中,积蓄着冲破泥土的力量,等待着一个复活的黎明。“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祂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祂。”(诗42:5)这多像我们的人生——破碎的誓言、未愈合的伤口、抽屉里积灰的梦想,都成了暗室中的银笛。但上帝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参林后12:9)
二、忧闷:海啸中的独木舟
诗人撕开伤口,任咸涩的血与泪流淌成诗。他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 三次叩问,如同三记重锤,毫不留情地凿开人性的层层伪饰与褶皱。
忧闷(hāmâ),在希伯来语中,是如同海啸般汹涌的咆哮,裹挟着毁灭一切的力量;烦躁(hāgâ),则是困兽在无助地舔舐着伤口的低沉嘶吼,充满了绝望与痛苦。我们却总是习惯于给疼痛包裹上一层甜蜜的糖衣,小心翼翼地称之为“压力”、“焦虑”,仿佛只要贴上一个轻描淡写的标签,便能够轻易驯服狂暴的风雨。但是,那位写下诗篇的智者,却断然拒绝这种虚假的粉饰太平。即便身处圣殿坍塌、百姓惨遭掳掠的悲惨流亡途中,他依然选择勇敢地直面自那片荒芜的废墟——没有了曾经熟悉的圣乐,没有了象征救赎的祭物,只有那些被无情拔除根须的橄榄树,在异国他乡的风中无助地摇曳,发出令人心碎的叹息。
这让我仿佛也回到了自己遥远的往昔。当曾经蜷缩在冰冷的病床上,看着输液管如同没有生命的透明蛇般紧紧缠绕住手臂,感受着监护仪上那令人不安的绿色光芒在墙壁上机械地跳动时,我的内心也曾无助地俯伏在上帝的脚前,听见自己心底那无法抑制的咆哮:“上帝啊,祢为何要掩面不顾?!”那一刻,仿佛也成为了诗篇的作者,成为了那在苦难中向上帝发出质问的约伯,成为了所有在炉灰之中紧紧攥紧自己拳头,与命运抗争的人。就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中,暗室中那支尘封的银笛,却又仿佛在轻声地提醒:忧闷,并非信仰的敌人,恰恰相反,它往往是通往真实的唯一窄门。
三、仰望:将脊椎绷成弓
“仰望”,这两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却是一个充满了挣扎与痛苦的动词,仿佛带着荆棘的尖刺,每每触碰,都会带来难以言喻的刺痛。
当摩西在旷野之中,举目仰望那高高挂起的铜蛇时,肆虐的风沙正无情地撕扯着他饱经风霜的脸庞,也模糊了他记忆深处那些曾经无比辉煌的画面——红海分开时那如同奇迹般耸立的浪墙,抑或是清晨降落时那甘甜如蜜的吗哪。在无情的现实面前,都已然褪色,变得模糊不清,如同墙壁上那早已斑驳脱落的壁画一般。百姓们被火蛇无情咬伤后的哀嚎声,声声刺耳,就在这绝望的氛围之中,上帝却出人意料地命令他铸造一条铜蛇,并将其高高地悬挂在杆子上。
“举目”——这个动作,又是多么像在竭尽全力地将自己早已疲惫不堪的脊椎,强行绷成一张满负荷的弓,将自己那充满怀疑与痛苦的目光,炼化成一支利箭,奋力地射向那颗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也依然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闪烁着的、象征着希望与应许的晨星。而哈巴谷的举动,则更是显得近乎荒谬:即便无花果树不再发芽,葡萄树不再结果,羊圈里的羊羔也已然绝迹,他却依然坚定地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参哈3:18)
童年时,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小心翼翼地埋下几粒种子,然后,便日复一日地,满怀期待地蹲守。直到某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一株嫩绿的新芽,终于顽强地顶开了那坚硬的外壳,破土而出,它那稚嫩而又略带蜷曲的叶瓣,如同一个婴儿紧紧攥着的拳头,紧紧地攥着一把金色的阳光。加尔文曾说过,真正的信心,是“即便身处无尽的黑暗,看不见任何希望,依然能够纵情歌唱”。在那些我们肉眼无法看见的幽深之处,生命的根须,正默默地编织着一张迎接复活的巨网,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四、赞美:水槽中的圣殿
赞美的力量,在于它像一把精巧的雕刻刀,能将寻常之物琢出光辉。
当诗人称颂神为“脸上的光荣”,便是在短暂的容颜上镌刻永恒。曾几何时,利未人在圣殿吹奏银笛,音波回旋于廊柱间;如今,跪在厨房瓷砖地上,水槽堆满碗碟,却从水龙头滴答声中,听见赞美的旋律。洗碗泡沫在阳光下泛起虹彩,恍惚间,竟似至圣所幔子上基路伯的刺绣,带来慰藉。
特蕾莎修女的祷告,是贫民窟绝望裂缝中破土而出的新绿,点燃希望;朋霍费尔在冰冷狱中写下的书简,则是透过铁窗,看到的闪烁星群,指引方向。而我们的赞美日志,也可以如此记录: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房间,三只活泼的麻雀便迫不及待地飞到阳台上,为了争夺地盘而激烈地争吵着,它们扑棱着翅膀,抖落的绒毛,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如同一个个小小的降E调音符,演奏着一曲充满生机的晨间小调;
午后,孩子们用手中的蜡笔,在洁白的纸上,认真地画着一颗歪歪斜斜的爱心,鲜艳的红色蜡屑,不小心沾在了桌角,为这平凡的午后,增添了一丝童真童趣;
黄昏时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过后,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柏油马路上,静静地漂浮着一片金黄色的银杏叶,叶子边缘那精巧的锯齿,则像是上帝亲笔签名的花体字,充满了艺术和神秘感。
五、复活的语法:泪滴作为韵脚
暗室中的银笛被再次吹响,尘埃在光柱里翩跹起舞。
3000年过去,笛声依旧低语:赞美的音准,不在于风暴是否停息,而在于灵魂是否甘愿成为共鸣箱。诗人说“我还要赞美祂”,这“还要”是绝境中的盼望:如沙漠甘泉,如雪地星火,如妇人于空坟前手捧没药——纵知死亡气息未散,仍固执地预备膏抹生命之王!
C.S.路易斯在《痛苦的奥秘》中写道:“神并非高高在上的哲学家,冷眼旁观苦难;祂是进入苦难,与我们一同承担的救赎主。” 妇产科的医护人员,每日见证着新生命诞生的艰难与喜悦,他们会温柔地鼓励着正在经历剧痛的孕妇:用力喊出来!你的呻吟,会帮助宝宝更快地降临到这个世界。原来,我们的哀哭与赞美,都是推动新生命降生的强大力量。每一滴饱含痛苦的泪水,都可能成为一首新歌中最动人的韵脚;每一道刻在心上的伤疤,都可能成为一个关于复活与希望的故事里,最值得铭记的标点。
六、暗室之外:光在裂缝中疯长
此刻,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温暖的台灯光晕温柔地包裹着我的肩膀,窗外传来阵阵轻柔的梧桐叶沙沙作响的声音,仿佛3000年前那支饱经沧桑的银笛,正穿透时空那道无形的裂缝,轻轻地对我说:不要害怕,将你所有的叹息,都谱写成一首动人的诗歌吧!
这看似黑暗的暗室,原本就是孕育光明的温暖子宫。当那充满力量的赞美之歌,如同银笛般,勇敢地刺破这无尽的幽暗时,我们终将会惊喜地发现——
那些我们曾经以为已经被彻底埋葬的,其实都正在悄无声息地复活,积蓄着破土而出的力量;
那些我们曾经无奈地称之为“废墟”的地方,如今也正在顽强地生长出翠绿橄榄枝;
而那支曾经沉默了整整3000年的银笛,此刻,也正充满期待地在你我的喉间,轻轻地震颤着,等待着一阵充满信心的和煦微风,将它吹奏成响彻天际的、宣告生命的复活号角!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