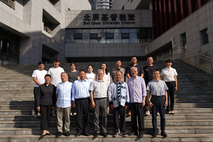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神学”只是“有关神的言说”。故此,词源学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基督教神学是有关哪一位神的言说以及怎样的言说。“神学”的定义只能来自信仰群体的特定神学立场。虽然如此,我们仍需要用理性去说明自己的神学立场,尤其要对自己所信奉的权威有清楚的解释。比如,对于基督新教来说,基督教神学乃是建立在三个唯独的基础之上,而在三者中,“唯独圣经”又是基础中的基础。基督新教的神学思想必须建立在“圣经”的教导之上,以“圣经”作为信仰的规范及真理的准绳。虽然如此,我们仍需运用理性去说明,新教的基督徒们为何以“圣经”,而不是别的什么来作为他们终极的权威。
一、基督教神学的来源
许志伟博士在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中提到了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四种来源,分别是“启示”“理智”“传统”“经验”。在这四者中,“启示”往往提供了信仰的内容,“理智”虽不提供内容,却能影响人对“启示”的理解,“传统”是人诠释“启示”的重要参照,而“经验”是“理智”的必要平衡。既然基督教神学的来源不止一个,为什么基督新教要以“圣经”,而不是别的要素来作为她在信仰及神学上的权威呢?
二、基督教神学的权威
在此,我们可以使用排除法来论证“圣经”的权威。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新教为何以“圣经”,而不是“启示”来作为她的权威。有关“圣经”与“启示”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圣经”就是“神的启示”,而“启示”只是包括了“圣经”。“启示”的外延更宽。“神的启示”包括了“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圣经”还不是“特殊启示”本身,而是“特殊启示”的保存。“圣经”是圣灵的默示,正因如此,它才能成为特殊启示的保存,也因而具有与特殊启示同等的权威。
既然“普遍启示”也是“神的启示”,为何不能与“特殊启示”具有同等权威呢?的确“普遍启示”也是神圣的,它与“特殊启示”一脉相承,共同见证神的奥妙。即便如此,我们不该忽视罪的因素。换言之,即便“普遍启示”也是“神的启示”,也具有启示神奥妙的功用,但人的堕落,使他无法对“普遍启示”有完全正确的认知。纵然神借着大自然将自己的永能与神性显明出来,使人无可推诿,却并不表示,人能透过这些启示可以正确地认识神,并与他建立合宜的关系。
其次,我们要来看一看“理智”。“理性”虽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能检验某种神学理论是否前后一致,并使人对基督教信仰有合理的认知。但其本身并不提供信仰的内容。事实上,“理性”必须建立在某种特定的信念之上,才能以这个信念作为其推理的起始点。离开了特定的信念,理性自身是无法正常运作的。比如,在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抬头,以自己为衡量真理的准则。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一批学者开始对“圣经”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他们剔除了“圣经”中的那些超自然性质的事迹,因为那些事迹违反了理性主义的原则,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当他们宣称超自然主义性质的事迹不符合真理的时候,他们是以什么作为标准的呢?如果说他们以“理性”作为标准,那么这样的回答仍是含混不清的。因为“理性”本身并不能证明“超自然的事迹”是“非理性”的。事实上,那些人并不是以“理性”来批判“圣经”,而是以那些隐藏在理性主义背后的形而上的信念作为特定的标准。他们预先假定所有超自然的事迹都是不可知的,是违反科学的,故此是不可接受的。
那么,“传统”又如何呢?如果说六十六卷的新旧约圣经是基督新教的信仰及神学权威,那么这六十六卷的圣经是怎样产生的呢?难道不是教父及主教们开会后决定的吗?换言之,六十六卷的新旧约圣经明显是在教会历史的脉络中成型的,凭什么说“传统”就不能在“圣经”之上呢?应该说,“传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基督教信仰、神学及教会的发展都是在历史的脉络中进行的。在“圣经”的成型方面,我们也应当从历史的脉络去了解其全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发现,新旧约各卷的成书与被正式接纳为正典作品之间往往有一个巨大的时间差。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被筛选的过程,不过主要乃是被教会筛选。因为教父与主教们在讨论正典作品的时候,主要乃是根据这些作品在教会中被接纳的状况来作出判断的。凡是真正的正典著述不仅会得到全体教会的接纳,更是能产生明显的属灵功效,以便显明圣经的权威乃在圣灵。这样看来,“圣经”固然是在“传统”中成型的,但“传统”并不产生“圣经”,“传统”只是承认了“圣经”并他的权威。
最后就是“经验”。“经验”诚然重要,但“经验”本身是模糊的,并不能清晰地表明神的真理。另外,如果将“经验”当成权威,那么基督徒所信的神就有可能只是人类经验的自我投射而已。故此,“经验”只能成为辅助的要素,而绝对不能成为信仰及神学的权威。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