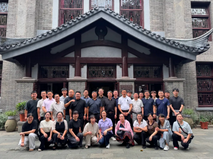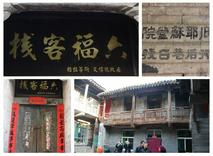一、基督教能成全“创化的进程”
赵氏虽然肯定达尔文的发现,却并不完全赞同其理论,因为该理论存在严重缺陷。他认为,若无宗教的辅助,进化论甚至可能产生反进化的作用。赵氏主张天演历史不能一概而论,应分两个不同阶段来看待,这一观点虽源自柏格森的创化论,但他特别强调人类的出现才是真正的历史分水岭。人类的祖宗是在“毫无知识的危境中”为后代创造了“可以比较不迷信的世界”。他们所凭借的不仅是理性,更是信仰。由此可见,人格与信仰密不可分,人类进化与宗教发展是息息相关,同步进行的。
那么,基督教如何成全这一进程呢?既然“创化”的关键在于人格,而人格创新又离不开宗教,基督教的独特性就应当体现在人格创造上。进化论者认为“人由兽进化而来,故人性易显兽相,难达人格”;但基督教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其目的在于“使人脱离兽性,达至神所赋予的神性”。这一观点有历史为证。
若有人否认基督教的贡献,只能说明其无知或故意“捣乱历史的事实”。因为基督教的贡献不仅改善了总体的社会环境,更能激发普通人性的巨大潜能。即使现今世界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改善,也不能证明基督教的无效。相反,世界仍然没有“极其改善”,是因为“基督教受了阻碍”,或尚未“完全得到最要紧的机会”。
二、基督教能成全“新境的理想”
1、个人方面:以耶稣人格为道德生活的源泉
赵紫宸认为耶稣的人格无疑是基督教的“中心点”与“根本”之所在,否则“什么十字架、什么登山宝训、什么救法、什么教会,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实用和益处”。
那么耶稣的人格如何能对信徒的生活产生影响呢?就是要将“耶稣培养在吾人心里血里”;就是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
具体来说,就是效法耶稣的信仰,效法他在认识神这条道路上的“身体力行”,每个人都需要与神建立“心灵感通”的关系。因为耶稣所启示的神是具有人格的全人类之父,能与每个人沟通,是可经验的。赵紫宸本人就是如此实践的。这种“灵交”并非是神秘主义的“空想”,是基于遵行神旨意而产生的宗教觉悟,因为“从行为而知道是非,从意志而得经验”。
只要人们践行耶稣的生活方式,就能体验到神的圣善美备,而这样的经验是不能缺少的:“我们可以无玄学上的假定与确定而生活,但不能没有耶稣那种从实际经验中产生的对于神的觉悟与热忱、信仰与安慰、诚服与快活、事业与生命。”
2、文化方面:促进社会制度与文化要素发展
科学:科学不仅不能废除宗教,反而还需借助宗教的精神:“科学含有宗教的完全诚服真理的精神……在我看来,科学用最崇高最勇毅的方法教训吾们基督教里全顺帝旨的大真理……”
哲学:哲学虽更具理性优势,却不及基督教有“效率”,因为“《圣经》的道集在灵通,哲学的理论所难到”。这种由灵通产生的宗教生活与经验正是哲学的源泉,因为哲学应当基于人生的实际,而不当单单依靠逻辑的推理。
美术:基督教是西方美术发展的渊源:“基督教没有流布之前,西方美术,都是威肃呆滞、孤特整齐的……后来基督教盛行,美术因了《圣经》中所载的威严慈爱的神和可贵能救的人类,种种神秘的、人道的、自由快乐的教义,一变其精神与性质。”因此美术永远无法替代基督教,“真正的艺术成就源于宗教”。
新文化要素:即“人道主义,人格尊严”,源于《圣经》训导:“近代新文化中所有的公义、博爱、同情、平等、自由,皆是《新约》中的要训。”若没有这些元素,文化就“不能有生命”。而这些要素之所以能成为文化的精髓乃因基督教与人类在道德心灵上有“共同追求”。
3、社会方面:教会与天国伦理观成全社会理想
赵紫宸神学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其天国观,那完全是今世的,丝毫没有半点彼岸主义的色彩。他理解的天国是无形的爱之境界,而非看得见的社会组织,强调基于个人生活的精神交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发挥基督教的两大特质:
首先是建立此种爱境所需的伦理关系。赵紫宸认为耶稣的伦理主要是建基在“神是父”的观念之上,并由此而衍生出两个维度:首先是神与人之间的伦理,其次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神是父”意味着他爱所有人,且每个人都宝贵:“神为父,所以凡为人者,无论何种何族,男女贫富智愚贤不肖,都是神的子女”。因此神就是爱,他的爱是“无物不覆,无美不载,无人不纳,无微不至”。就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而言,“神是父”意味着人人都是真弟兄,应当彼此相爱。
其次,乃是实现此种爱境所必需的组织基础——教会。尽管它只是实现天国的工具,却也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若没有此工具,天国便无从开拓。因为爱的境界是从宗教生命中流露出来的。因此有形的教会需要革新自己的功能,切实践行耶稣的教训与爱的生活,而不是在教义教规上面徒作辩论。当然这并不能完全排除组织的必要,为了成全圣徒相通的生活,“教会要有学行兼优的牧师,更要有学行兼优的平信徒用实力去辅助他”。
总之,教会成员应当“彼此切磋砥砺,共立行谊,共负责任,共事上帝,共救同胞。如则锻炼宗教的热诚,出则注射真理的光华。教会贫苦则慷慨解囊,倾家荡产以救之;教会艰难,则舍生取义,赴汤蹈火以扶之”。这样的教会乃是天国的雏形,在它里面“人人有工作,人人有负担,人人有生命”,如此便成全了“人人都是弟兄,人人都能互助,都得了应得名分,享了应有权利,存了真切的生活”之新境所要求的理想社会。
引注: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赵紫宸文集第一卷》;
赵紫宸,《宗教与境变》,《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约翰·麦奎利著,何菠莎译,《二十世纪宗教思潮》;
赵紫宸,《耶稣的人生哲学》,《赵紫宸文集第一卷》;
赵紫宸,《罗素的基督教观念的批评》,《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对于“信经”的我见》,《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新境对于基督教的祈向》,《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我为什么要读“圣经”?用什么方法读“圣经”?》,《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耶稣的上帝观》,《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圣经”在近世文化中的地位》,《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万方朝圣录》,《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促进宗教革新的势力》,《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