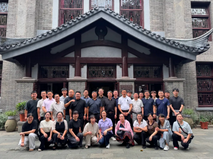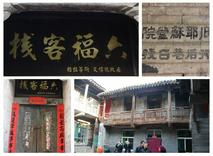一、在应境中发现真理
1、真理的权威
赵氏认为“凡能发生影响的即是真理”,它是相对的,其标准乃在理性的判断,即“公认的学权”与“社会的经验”。否则当各人都持定自己的权利时,“岂不要把《圣经》的权威,移到各人自身,各党自身,名为《圣经》的权威,实则为各派的权威,转成了……‘个人是真理的权衡’的怪现象吗?”另外,经验的层面更是显而易见,因为“若经上所谓感通、赦罪、得慰、成圣种种理都可以从信仰接纳而成为经验;都可以使吾人听其命令,不能不从;都可以成为从许多个人推至社会而为社会共有的生活……那么《圣经》在人的经验上必然要得无上的权威。”
2、圣经要义的探求
既然圣经的权威在于公认的学权,那么学权的理性又是依据怎样的原则呢?赵紫宸认为与传统相比,此种理性具有明显的科学性质,而这种科学又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由于进化论清晰地凸显了历史演进的过程及其意义,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智识界所依据的原则。透过演进的历史,才能发现《圣经》的真义。原来,《圣经》并非一成不变的灵感书,或科学书或具备严密统系的哲学书,“乃是一部宗教道德的丛书”,是神透过人的经验而来的启示,因此是“随人程度的增长而进步”。
耶稣乃是启示的集大成者,而他的人格也便成为了启示的聚焦点。这样,信仰虽然奥妙,却不是奥不可测,因为信仰的奥妙乃彰显在人生之中。人生的经验就不会遭腐蚀与破坏,反而因着神秘的灵交,胜过罪恶的力量,使进化有利于人性的发展,而不至“回到草眠禽兽的状态”。
二、在应境中发现伦理
既然真理是相对的,有着显著的时代性,那么在教会,必须反思基督教教义的适切性,具体来说,即《信经》所代表的基督教教义是否具有时代的特征,切合当代人的需要。在“对于《信经》的我见”一文,赵紫宸表达了他对《使徒信经》的不满:
第一,“里面挟些不是信条的话”,“被难”等语“全是历史的事实,并不是信仰的条件”;第二,“《使徒信经》含有不关紧要的话”,赵氏认为“童女马利亚所生”及“肉体的复活”二语根本就是与科学抵触的信条,并且更是与人生德行无关重要的事,倘若无谓的坚持只会让寻求真理的人望而却步;第三,“《使徒信经》不包含许多重要的信条”,“罪得赦免,圣徒交通以及永生”等语,也只是含蓄的提法;第四,“《使徒信经》只重玄理神学,不提人伦道德,实在是个缺点”,虽然自古以来的《信经》都有这个弊病,但“处于今世”这个特殊的时期,若想要讲论《信经》或个人的信仰,则“‘伦理’二字,万万不可不仔细讨论研究”;第五,“《使徒信经》完全没有说起耶稣的人格,真是极大的缺点”。
这五个方面虽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括起来却只有一个不满,即对于忽略伦理道德而生的不满。赵紫宸认为《使徒信经》的根本缺点在于它是个重历史、神学、玄学而轻伦理的《信经》,而这样的《信经》所造成的信仰,是没有适切性与生命力,“在目今宗教道德运动盛兴的时候,如何能够邀人深信呢?”
因此,拟作《信经》虽会面对不少的难处,却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赵氏所拟定的新《信经》共有六个条目,与《使徒信经》相比,新《信经》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神主要是人“圣善慈爱”的天父,因此是人“道德的标准”;耶稣乃因着“圣洁的生”,“牺牲的爱”,“自建的人格”而为“神独一完全的儿子”,他与人类的关系乃是“师傅”与“徒弟”,他是善范,是人们效法的榜样;在圣灵的感化下便能与他“和睦,交通,同工,而得心灵的扩大,道德的发展”;这样,“凡与基督同心志,同生死,同荣辱,同勤劳的人”就是“基督徒”,他们都有“永生”而教会的本质乃在“精神的交谊”,“公会”只是“实现基督生活精神的工具”。最后是信仰的目的,即要达成“天国的实现”,而这个天国并不是传统所谓的彼岸世界,乃是指现实中充满爱境的社会生活。它是可以完全实现在地上:“故真理日入而愈彰,教会日久而愈兴,人类愈久而愈和合,世界愈久而愈文明。”以上所述,不仅含有浓厚的伦理色彩,还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基督教的独特性就是它相信借着对三一神的信仰,人们自我的努力以及彼此在精神交谊上的砥砺成就天国的伟业。
三、在应境中发现信仰
信仰的本质并非学耶稣做好事,乃是信仰耶稣所信的神。赵氏认为耶稣的神观也是一种应境的产物,不过,这个应境有一个具体的过程,简括来说,就是“承上启下”。所谓的“承上”即是承接先知的统绪,他们的神虽不是“机械的、远隔的权威”,不过他们因受神治主义的影响,并没有脱离“神是一族一国之父”之观念的限制,而耶稣却不然,因他以神为人人之父,这就是他“启下”的地方。
那么为何耶稣对神的认识能超越旧约时代的先知呢?因他对神有着“至密切亲近的灵交”,并且对着神的道能 “身体力行”。他的神观是彻底地“从经验中演绎出来的”。其主张不仅是用言语所阐明,更是“在他的行为上发挥出来”,叫人“见他如见父,近他如近父的。”
透过经验人们可以体会到这位神,是有活泼的人格,因此他是“男女贫富智愚贤不肖”,“无论何族何种”之人的父亲。不仅如此,他也是人类唯一的救主。虽然耶稣也为救主,然而拯救的意愿却是出于神。他更是拯救的原动力,因为耶稣也是由于“神人交通的成功”而成为人类之救主。这样看来,“神为救主”与“耶稣为救主”之间并不具有等同的含义:前者乃在直接的灵交;而后者的意义似乎在于“道路”或“榜样”,是前者所要达致的目标。
引注:
赵紫宸,《“圣经”在近世文化中的地位》,《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新境对于基督教的祈向》,《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宣教师与真理》,《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对于“信经”的我见》,《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耶稣的上帝观》,《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赵紫宸文集第一卷》。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