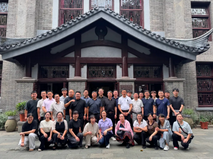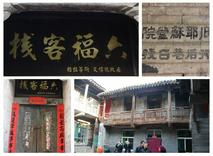虽然注重功能是赵紫宸神学思想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却仍不能简单地说他的思想是围绕着功能而构筑,因为这样的结论无疑会忽视他对基督教独特性的坚持。事实上,赵紫宸的神学思想有三个不同的范畴,即“独特性”、“相关性”及“功能性”。其中“独特性”与“功能性”乃立于现实的两端,一端是基督教自身所拥有的一切,另一端则是它所能发挥的社会功用。在这两端之间的是“相关性”,它是桥梁,使“独特性”能实现它独特的“功能性”。
那种视赵紫宸的神学为纯粹围绕着社会功能而构筑起来的观点,实际上是走了一条从“功能性”到“独特性”之间的反向路线。倘若如此,赵紫宸又为何要如此坚持基督教自身的独特性呢?难道从“功能性”到“独特性”的路只有一条吗?难道不坚持“独特性”便不能达到“功能性”的目的吗?若是这样,吴雷川与王治心等人又为何就不像赵紫宸那样坚持呢?
笔者认为,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厘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独特性”是真理的实体;“相关性”是真理的形式;“功能性”是真理的效验。如上所示,赵紫宸的神学思想虽以经验为核心,却并不意味着他的神学是杜撰出来的,因为真理的效验指向真理的实体,试验主义的宗旨乃在于以果推因。
因此,在赵紫宸看来,真理必须是真正存在的,否则便无法产生真实的效验,这也是他为何要与吴雷川划清界限的重要原因。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若赵紫宸的神学思想是围绕真理的实体而非其效验建构,那么他所指的真理应当是绝对且永不改变的。若是如此,又该如何解释他思想的易变性与多样性呢?笔者认为,赵紫宸的神学思想虽常呈现易变特征,却并非无迹可寻。从早期的自由主义到晚期的新正统主义并非毫无预兆的突变,而是有前因后果、朝着特定方向渐次演进的。
在“功能性”方面,赵紫宸始终坚持基督教能塑造善美的人格,并由此开创新的文化生活进而改变整个世界;在“独特性”方面,他始终相信基督教有“真迹”,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与动力来实现这个目标。然而,当赵紫宸最初面对新文化运动与非基运动的巨大挑战时,难免有急于求成之失,试图借助中国文化这个媒介来实现人格革新的目标。
不过,当他过于依赖“相关性”时,基督教的独特性便被淹没,人格救国的宏愿竟沦为虚幻的空想。故在三十年代,赵紫宸将重点转向对独特性的追寻。但当他如此做时,却发现自己的思想反成了眼前的拦阻,因为这些经过中国化的思想不能为他提供属灵的动力,社会重建的目标再次遭到重创。直至经历狱中苦楚,他才猛然醒悟早年的思想何等幼稚、肤浅与有害,于是彻底抛弃自由主义观点,转向新正统主义立场。
因此,赵紫宸神学中的“独特性”表面看来虽不断变化,却有统一的根源——那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新正统主义,而是他留美之前基于人生经验的感悟:“宗教——基督教——无他,亦神与人我,人我与神感通交和而已矣,耶稣特为此中和通格的表显而已矣。”当然,这层感悟需要获得理性疏解,这正是他在美留学及回国教学期间进行的神学思考与转化——将早年所得感悟透过神学架构建立起与环境的关联,形成相对固定的神学理论。唯有如此,才能使这个“独特性”透过“相关性”生发出其独特的“功能”来!
引注:
唐晓峰,《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
邢福增,《寻索基督教的独特性——赵紫宸神学论集》。
约翰·麦奎利著,何菠莎译,《二十世纪宗教思潮》。
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导言》《赵紫宸文集第二卷》。
赵紫宸,《我的宗教经验》,《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