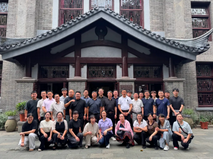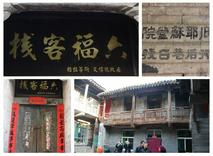1、宗教与美术
由此可见,赵紫宸的神学是一种十分注重功能的神学。这与他早年的时代背景有着很大关系。在五四风潮的狂飙下,一切传统权威都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宗教自然不能例外。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安排了一系列有关宗教辩论的演说,参与此次辩论的学者虽对宗教持有不同看法,却存在一个重要相似点,即大多从功能角度评论宗教问题。
其中蔡元培的论调尤为突出,他认为宗教的功能主要在于满足人们情感上的需要,因此一旦某种文化元素能像宗教一样满足人们在这方面的需要,它就能取代宗教的地位,使其彻底失去存在的基础。蔡氏所指的这一元素就是美育,故有“美育取代宗教”之说。
面对如此情形,赵紫宸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蔡氏的说法无疑是一种武断的偏见,源于对西方美学源流认识的不足。要澄清“美育能否取代宗教”这一问题,需要正确认识美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首先,宗教不是美术,因为西方的美术受宗教影响而提升:
“基督教没有流布之前,西方美术,都是威肃呆滞,孤特整齐的……后来基督教盛行,美术因了《圣经》中所载的威严慈爱的神,和可贵能救的人类,种种神秘的,人道的,自由快乐的教义,一变其精神与性质。试问欧洲的大礼拜寺,其尖顶如手掌之向天祈惠,其装饰如情绪之随时应变,较之希腊的巴西朗(Parthenon)的徒有完备几何的比例何如……”
其次,宗教不是美术,因为宗教是完全的生命,而美术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宗教若单是情感,美术或者可代,也未可知;生命若单是美的情感,美术或者可以维持他,也未可知。反而言之,美育若能创造新信仰;若能将人生一切希望价值融和统一在美术的范围里;若能固定人和无形境界的灵通,实现人格全体的交换与尊敬,使人得最崇高的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若能为人解决一切忧痛悲惨问题,度一切罪恶苦厄;若能把人生的原妙一切阐透打破;则美育就可代替宗教了。”
这样,赵紫宸最成功之处,在于理清了宗教与美术的关系:首先是两者在本质上的差异——宗教是生命之源,美术是生命之体,后者必须依附于前者才能成长,何谈取代?其次是功能差别——宗教是生命的全部,美术是生命的一部,若以美术代宗教,岂不是以偏概全?因此,“文化中间,不可一日无美术,但美术不能一日代宗教。美术不能一日代宗教,世上再也没有一件文化的元素可以代替宗教了”。
2、宗教与社会
既然宗教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在实际领域中它又有怎样的功能?能为中国社会的重建提供怎样的独特贡献呢?在《罗素的基督教观念的批评》一文中,赵氏驳斥了罗素关于登山宝训的谬论。罗素认为登山宝训只是冠冕堂皇却又不切实际的高调罢了,并不能在平常人群中生产生实效。赵氏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罗素的最大错误在于其观点只是一种空想,不符合历史事实:
“自从基督教流布以来,为道舍生的人,历尽了刀剑、岩穴、监狱、戏院、兽类的种种危险苦难,仍旧把道理传到敌人中间,到如今文明野蛮民族里,都有基督的生命流通,难道这不是耶稣宝训在平常人性上的效率吗?难道千千万万爱人的门徒,舍生的信者,都是非常的人吗?若都是非常的人,为什么基督教里非常的人如此其众呢?”
面对新思潮对合理生活的迫切要求,赵紫宸询问:基督教能为中国民众提供这样的生活吗?倘若“基督教不能贡献合理的生活,除仪文传俗之外,没有文化必需的元素,人生必须的力量,那么基督教不能再有应当的存在,我们大家不必再奉此教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西方列强的肆无忌惮与军阀割据的明争暗斗,促成了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尽管如此,中国社会的情形似乎并未好转。是这些运动不够深入彻底?还是缺乏既定方向与统一部署?或许皆是,但赵紫宸认为根本原因不在此。他指出,中国的问题不在其他,而在中国人自身。因此,人格问题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为回应时代挑战,当时基督教界发起“人格救国”倡议,与赵氏志愿不谋而合。于是他以人格为主旨,以《宝训》为蓝本,撰写了《耶稣的人生哲学》,并将此书献给该运动创始人——余日章博士,视此为无上光荣。
由于赵紫宸以人格改造为救国方略,他的神学绝不以构筑宏伟思想体系为目标。相反,他甚至认为与实际人格相比,神学贡献乃属次要。因为本色化的关键不在神学家是否构筑了恢宏思想大厦,而在基督徒是否活出本色化的人格生活。人格是生命的全部,是生活的渊源,是文化的种子,没有刚毅人格便不可能有善美文化。
由此可清晰看出,赵紫宸的神学思想完全以人格所示的经验为核心。他认为,在这个理性至上的世俗氛围中,基督教只有一条出路,即以对社会的特殊贡献证明其合理性与存在必要性:
“基督教的试验,不在于她能否从她的束缚捆绑中得解放,而在于她能否既超遗传而复能独得理解,使真理得成生命之流;不在于这教义,那教义的成立与推翻,而在于她自身的内心生活全部,能否示现于我国国人生活中;不在于这宗派,那宗派合并不合并,统一不统一,而在于她能否使人类统一于实际的磐石上,由此而显示一切价值的关系。不在于中国人的理解如何,而在于全世界的信徒有没有比较满意的理解;不在于她能否阐明自身的意义,而在于她能否阐明人生的意义而使人生超脱兽性兽欲的羁绊。不在于她能否拯救这个人,那个人,而在于她能不能综合世界的文化,统一人类的精神。”
引注:
林荣洪,《曲高和寡:赵紫宸的生平及神学》。
赵紫宸,《「圣经」在近世文化中的地位》,《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罗素的基督教观念的批评》,《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新境对于基督教的祈向》,《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编辑者言》,《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耶稣的人生哲学》,《赵紫宸文集第一卷》。
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赵紫宸文集第三卷》。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赵紫宸文集第一卷》。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