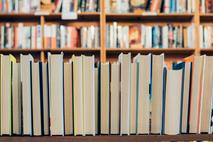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题目是一个大题目,不太好写。中国、西方的认知和交流是一种漫长的过程。关于中国与西方的相遇、交流和对话,属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大课题,这方面的著述亦浩如烟海。在此,我们对之仅加以粗线条的点评和分享。
说到现代中国文学,不能避开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影响。1940年,我国著名的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专家、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代大师级学者朱维之先生在《基督教与文学》一书的导言中说:“我国近年来接受西洋文学,努力研究,介绍,作我他山之石。这无疑是有价值的努力;但在这项努力之中,要密切注意两种思潮,不可偏废。二十余年来我国新文坛偏袒异教思潮的态度,非稍加矫正不可。须知基督教在文学中永远占着重要位置:古时代在中亚,中世纪在南欧,近代在全世界文学中,都演着主要的角色。古代和中世纪固不必说了,就在近代异教思潮澎湃的天下,基督教仍旧占有半壁锦绣的江山。”(详见高旭东等著:《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
基督教文化影响和催生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等新文学模式,是将圣经典故作为作品的文心,用其叙事框架作为文学的叙事模型,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转型和发展。例如,由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到公元纪年的转变、基督教节日进入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系统、基督教的一些词语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时间中染有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具有了迥异于传统的叙事风格。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式从“反对论”“契合论”“矛盾论”发展到“整合论”,解构了传统的纯文学本体研究范式,激活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相对停滞的局面,取得了一批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与基督教文化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一、基督教的进入融合了中国的现代文学
督教文化的进入打破了中国文学的封闭性,促使中国文学对世俗与终极、批判与超越、自我与世界、身体与精神等问题有了复杂的关注和回应,创造了中国文学新型的传统意义和表达方式。
晚清,基督教即开始在中国传教,并在文化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禁闭百年的门户被打开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为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道光皇帝于1844年、1846年先后颁布敕令批准弛禁天主教。此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办报,比如创办于1854年的《中外新报》,由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是基督教在华较早的中文报纸之一;办学,比如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1904年创办,正式校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联合开办,鼎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金陵大学(Jinling University):1888年创办,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编类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持有金陵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是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1900年创办,其法学院尤为著名,被誉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培养了中华民国外长、总理、著名法学家王宠惠,著名法官、法学家吴经等;出版译著,比如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办医院,如:北京协和医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1835年由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创办,这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建育婴堂,设孤儿院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蓬勃展开。
纵观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历史,我们可以十分真切地看到,一种外来文化的全面传入,总会有一个与本土传统文化的冲突碰撞的阶段和过程,而对本土传统文化的了解与研究则是使异域文化真正能够进入的前提。外国传教士大多注重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努力以中国的传统典籍阐释基督教思想,并极力获得帝王的传教许诺,发展与士族阶层的关系,以此而影响中国社会。鸦片战争之后,由军事入侵而带来的传教便利,却形成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畸形发展。一个国家或民族处于强盛时期,常常对异域文化采取一种宽容大度的政策,从而促进其与本地文化的交融相汇;而当一个国家或民族处于衰弱之时,它常常对异域文化采取一种封闭排斥的做法,使其传播中途夭折。
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封闭已久的门户,打破了中国士大夫们将华夏视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内夏外夷、用夏变夷的心理定势也受到了冲击,儒家的礼乐教化、纲常伦理也不再是天下文明的唯一尺度。面对门户被打开以后的外面世界,中国有思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充满了一种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经过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中国知识分子更加深切地感悟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深入反省批判的紧迫性,对西方近现代文化学习借鉴的必要性,对中国广大民众进行启蒙的重要性。加之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中,以办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和育婴堂、孤儿院等慈善事业相辅助,不断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使人们对基督教逐渐改变了以往极为仇视的态度。
20世纪初,传教士们在传教过程中,常常提出一些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喊出一些引起人们共鸣的口号。如李提摩太提出了“救个人、救国家”,基督教青年会领袖穆德和艾迪提出了“如何救中国”、“中国的困境与出路”、“中国之希望”等问题,这些都促进了传教活动,扩大了基督教在民众中的声誉和影响。“其实,随着西方列强殖民主义对中国各地的不断侵入与渗透,首先冲击近代中国人精神价值世界的,倒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跟随着枪炮、商品之后大量涌进中国本土的基督教。”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基督教的思想也常常为人们所汲取。
二、现代中国文学也源于有识之士接受基督的思想
文学现象是历史和时代交织的产物,考察其意义和价值应将其置于这些历史与时代的背景中,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渗透了基督精神的五四时期的文学作为一个中国文学史上特意的文学现象,出现于五四文坛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其中不乏现代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接受基督教的思想,这种情况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深刻的熏陶。
由于基督教各派通过鸦片战争后的不平等条约而进入中国,使中西文化冲突与政治冲突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基督教被多数中国人视为与中国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洋教”,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受到多次抵制和反对。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全国共发生针对教会的大小教案400余起,形成影响深远的反洋教运动。在中国知识阶层中,这一时期对基督教的反应则是颇为复杂的。例如,多次应试失败的文人洪秀全(1814-1864)受基督新教的启发而创立了拜上帝会,发动起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他对传统中国儒学持排斥态度,曾毁弃孔子牌位、关闭传授儒学的村塾。虽然他因“多发奇想”、理解过于偏颇而不被教会接受,未获得罗孝全(IssacharJacob Roberts, 1802-1871)的施洗,其同道冯云山和洪仁玕却在此间正式领洗入教,因此在这一农民起义中多少引入了一些基督教的观念。洪秀全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1843年创立了“拜上帝会”,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提出“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门,循行上帝之真道”的思想。这种实践多少反映了基督教与中国下层文人结合中的尴尬局面:拜上帝会及太平天国既不被视为基督教的“正宗”,也不被看作为中国社会所不容的“邪教”。
康有为曾“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他谈及基督教时曾说“然其所长者,在直接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曰人类平等也,皆上原于真理,而下切于实用,于救众生最有效焉”。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然而基督教的长处在于直接和纯粹,专注于一个核心教义,深刻而鲜明地指出:人类是同胞,人类是平等的。这些观点都源于真理,同时又紧密结合实际应用,对于拯救众生最为有效。康有为曾以基督教的马丁路德自称,构想他的大同理想世界。受洗入教的孙中山更加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他自谓“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在宗教信仰方面,推崇耶稣基督;而在人物榜样上,则敬仰中国历史上的商汤、周武王,以及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孙中山汲取基督教思想助成其三民主义,认为“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教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因而人称:“孙中山革命的抱负,及其所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挠,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努力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全力从西方文化与思想中寻觅解救中国的良方,基督教思想也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汲取与借鉴的西方文化思想之一,不少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倡导汲取基督教的思想拯救民族的命运,其中以陈独秀的倡导最有影响。陈独秀虽然在1918年的《偶像破坏论》一文中说:“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然而,他却在1917年《新青年》三卷第三期中答复读者时说:“宗教的价值,自当以其利益社会之力量为正比例。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陈独秀赞成以基督教思想作为批判否定孔子思想的有力武器。他在1920年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直截了当地说:“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的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种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陈独秀将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教会截然分开,否定基督教的创世、复活、神迹等圣事,而肯定基督教中的博爱、牺牲等思想。他充满热情地说:“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义,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的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那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1921年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出:“……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1922年胡适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一文,阐释宗教的伦理教训、神学体系、迷信成分的内涵。他认为,基督教的迷信是来自两千年前人的无知,应该摒除;神学体系是中世纪僧侣院士的推理,也不足取;耶稣的道德言训和社会改革,在理性尚未完全管治人类以前,是可以采纳的。胡适提倡宗教自由,将基督教视为一种道德宗教,认为应该容忍基督教,而不应盲目反对。1923年4月,著名作家许地山在《晨报副刊》发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一文,也极力推崇基督教为中国当时所需要的宗教。在这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倡导下,“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家对基督教文化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热情,在他们的创作中洋溢着浓郁的基督教色彩。
在孤寂病痛中的作家庐隐在童年的时候就十分虔诚地归向基督信奉了上帝,她期盼从上帝那儿获得她在人世间不能得到的爱,童年的她虔诚地祷告礼拜,并认真地向家人宣传基督。她说:“上帝是这世界上的唯一救主,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被上帝逐出乐园,所以我们这些人生下来也都有罪,除了信耶稣,不能逃出地狱。”她却遭到哥哥们的嘲笑,他们甚至撕碎她的《圣经》,干扰她的祷告,咒骂基督耶稣。庐隐说:“真的,那时节我为了哥哥们的毁谤耶稣,流过非常痛心的泪呢,我常常偷着替他们祷告”。
这些事实充分论证了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紧密的关系。
好,我们今天暂时分享到这里,请继续关注下篇。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