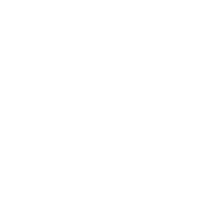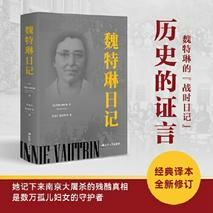老爸:
我还是用这个经常喊您的称呼开头吧。提笔写下这两个字,就仿佛看见您骑着那辆天蓝色的三轮自行车,到养老公寓的大门口接我的身影;又恍然看到您依旧蹬着那辆三轮车,送我去车站的背影。只是您不再说话,我也听不到您的喘息声了。因为疫情封控,我也不能去墓地看望您和母亲,想来想去,还是铺开信纸,把想说的话,一字一句写下来吧。
此时此刻,窗外长风呼号,黄沙漫卷,纸屑飞扬。也好吧,那就托长风捎去我写下来的每一个字,深愿它们蘸着我脸上正恣意流淌的泪水,化作一首安魂曲,飞翔到您那里。单曲循环着,播放给您听。
老爸,我握紧手里的这支笔,就像再次握住您的手,在一束又一束的微光回忆里,与您相遇,和您唠嗑。还清晰地记得,去年清明节前,我去养老公寓看望您,听我随口说了一句:想尝尝春天野菜的味道。您就趁着出去遛弯儿时,采回来几棵开着娇黄的花朵、鲜翠欲滴的蒲公英。据说它们长在一个土堆上。您是弃了那辆当做拐杖的三轮车,弯着腰爬上去,才伸手够到的(您说故意没有把它们都连根拔起,是想等它们再长出新叶子,还可以继续为我采食)。此举又印证了那句老话: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接着,谷雨前后,您口头指导我,种了倭瓜、丝瓜和花生;您捡来树枝,给西红柿搭了架子;还亲手把吃剩的肉膘埋在地里,说是这样,可以肥田,菜会长得壮实。果然,去年的西红柿大丰收了,“嘀里嘟噜”挂满枝头,一眼望过去,小红灯笼矮矮挂,哈哈!喜兴,好看。
老爸,我记得“二十四节气歌”是您最早教我背诵的,用滦南老家的特色方言,一字一顿地耐心教唱。您把清明的“明”字读成meng,那如唱歌般的独特腔调,和着夏夜的虫鸣,像一部打开的岁月留声机,款款诉说着一种古老、温馨的传承。
您没有学历,但懂得供我们念书。只要我们不是厌学,或者私自逃学,都一直支持我们求学。您从不随随便便喊我们各自的乳名,每次都郑重其事地叫我们的学名,大名。您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心目中对书香门第的崇敬。我知道,除了舐犊之情,还有您对儿女的一种尊重。这在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农村来说,是极其稀罕,极其宝贵的素质。
老爸,还有一个情景,至今令我感慨万千:出殡的当天,您的灵车路过四段(第八生产队)的庄头时,有三个熟悉您的乡邻,他们因着一份深厚的“老庄户情意”,知道您年轻时喜欢吹唢呐,就主动提出来,用这种特别的方式,送您最后一程。尽管过去了六十多年,他们依然记得您的喜好,用那或悠扬婉转,或高入云霄的唢呐,声声纪念着只属于您自己的一生。老爸,我想您一定听到了,也一定被安慰到了!您会像往常那样,孩子似的呵呵笑吗?
后来,听我姨说,母亲出殡那天,路过四段,竟然惊动了全庄的人都出来相送。那个宏大的场面,一时传为佳话。我听闻后,又惊又喜。惊的是,一个已逝去的人,到底是怎样高贵、馨香的品德,吸引了全庄的邻舍,自发来送别呢?我喜的是,你们虽然只是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平民百姓,却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亲爱的你们,高贵的你们,真是没有白来这世上走一遭啊!
老爸,您一生坎坷,所受的每一个荣辱,自有天道知晓,女儿不想在此一一赘述。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在有生之年,您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您生命的救主,祂因死里复活的大能,必为你负责到底。至于我,写下这封信,也让我思念的伤痛,缓解许多。
老爸,记得在天堂里照顾好自己呦,多和别人说说话,聊聊天,别再自己老闷着了。想说的话还有很多,就留待下一封信,好吗?
您的老闺女
于壬寅年清明节前夕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云南一名神学生。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