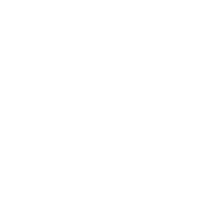忻若没来橘园之前就经常听说过无花果,但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来到橘园之后,她每天能看到生长中的无花果。
每当打开侧门,那一丛丛长满鲜绿叶子的灌木便是无花果。平时忻若一家人习惯于把这种果实和树都称作“无花果”。忻若喜欢它那宽宽大大的、形似手掌、色泽犹如半透明翠玉的叶子。无花果树和叶子都很香,它还会流乳汁,当你不小心碰落一片叶子,或故意摘了一片时,那雪白而粘稠的乳汁就会滴落下来。要是哪个调皮的孩子用小刀在树身上划一刀,乳汁就立刻倾注出来。此时,你所闻到的清香要比平时浓好多倍。
无花果吃起来甜甜的、凉丝丝的,质地很细柔,胜似香蕉。其形圆,大于枇杷,成熟时变软。皮色油亮,近于红紫,剥了皮就可以吃。橘园里有三处无花果,屋边的无花果、葡萄架边的无花果、苎园里的无花果。“它们都像那棵‘栽在溪水边的树,按时候结果子,叶子必不枯干’”看到这些茂密的无花果,忻若总会想起这句话,因为无论它们栽在哪里都长得那样好。
无花果还是一些飞螟的诞生地和温床。幼虫在树身里面生长、成蛹,直至飞离,而留在树皮外的痕迹仅仅是一个个小孔和一堆堆遗矢。然而不管被虫子咬得怎么样,无花果树还是照样生长。有的主干被咬得上下只连着一点皮,于是就地一倒便长出须根,扎入深土,生长如旧。霜降到来时,叶子逐渐稀疏。立冬之后,无花果慢慢地进入无叶期,但地下的根茎却无止境地延伸,早春一到便迫不及待地冒出新株,而所有的枝头也同时长出了淡绿色的嫩芽。这时忻若一家人无论分散在何处,都会心领神会地吐出一句:“当无花果发嫩长叶的时候夏天近了!”春芽给忻若全家带来了美好的希望,他们盼着:到了果熟的夏日,全家都能一同品尝这盼来的甘甜。
岁月在期盼中度过,一到深冬,忻若一家总是怀着新的希望,盼着来年的春芽……当叶窝里长出翠珠般的小果时,邻里伙伴们,从五六岁到二十几岁都忙碌起来;小的在后山腰选阵地、找石块、运黄土,晴天垒石碉堡,雨天湖黄土岗亭。等到叶子茂密,果实长大时,小伙伴们的“大功”也告成了。他们坐镇后山腰,居高临下,日夜坚守。小机灵们不时抛出大小石块,袭击了一阵之后,见无反应便可蹑手蹑脚地潜进来摘果吃。至于那些大伙伴们就无须花此等力气,只要早晚“打打游击”就能吃到无花果了。
无花果收得多的时候,每天也晒一些作为干果吃。晒干以后,禇先生还会分送给那些大大小小的“细儿们”吃。当叫到他们的名字时,一个个都会应声而来,甜甜地叫一声:“禇先生……”没叫到的也赶紧来“报到”。每人都分到之后,老先生提着空篮子微笑着目送篱笆外面那一张张满意的笑脸。于是这些孩子们便把自己领到的两个干无花果紧紧地捏在手心,慢慢退着走回去。当然,有时还可以分到一些葡萄干。
没有了橘园没有了无花果,可往日的无花果又仿佛一直生长在忻若的周围,它还是那样茂密,翠绿。忻若喜爱它那清新的乳香,它的顽强,它的甘甜!
忻若梦见自己蹲在亓山河边,“我来看你了!”看着潺潺的流水,忻若欢呼着。一只大篷船吱呦吱呦地划过来,船上堆满了一捆捆雪白的麻线,一个穿红外套和两个穿花衬衫的女子坐在麻堆边,船老大双手划着桨,不时腾出一只手扯自己脖子上的毛巾擦汗,浪花大半圈大半圈地打在埠头的石阶上、屋基边上……“他们真早啊!人家还没有上班呢!”忻若看着他们,又望望东面、亓山那边、树丛里刚刚露脸的太阳,自言自语地说。她们从里塘那个方向赶来,是给丽人台麻袋厂送麻纱的。街灯还亮着,灯下缝麻袋的女孩子已在那里“飞针走线”。这里还是往日的亓街,街面窄窄的,沿街的河道也是窄窄的。这里的河向来是无名的,只有忻若才把它叫做“亓山河”,在忻若眼里它就是母亲河,它虽然无名却是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船只陆续多起来,运货的、载人的,双桨的、单桨的,去市中心的,往新田以南乡村的,在亓街任何一个埠头,你只要招招手手,说一声“搭船!”花一二毛钱就可悠哉游哉地载着去你想去的地方,又快又省力,在那种去哪里都步行的年代搭“小船儿”是最花得来的。一只小船向埠头划过来,有人从忻若旁边上岸,有人在洗衣服,忻若用手划着水,一边划,一边掏出口袋里纸折的小篷船,轻轻地搁在水面上让其飘荡。它们顺流南下,又被南面来的船只划起来的水浪带了上来,在忻若面前停住、似乎不肯离去,又好像要对她说点什么,她双手托起它们说:“谢谢你惦记着我,还没走多远呢,去罢,顺着这条河过了梅园寺就可到大河——里塘河,在那里你就可以‘悠然见南山’了!”说着,忻若又把它们搁在水上。
来往的船只少了,忻若的小纸船飘到很远很远,在鹿山脚下成为一个小白点。忻若正望得出神,耳边响起了她祖母的喊声,“啊,该把苧拿到河里浸泡了!”忻若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童年……苧在水里慢慢泡着,鱼儿在亓山的倒影里游着或穿梭于苧竿之间。忻若一边掏出小纸叠船,一边等着这捆苧泡够时间,她折了一大堆军舰,用草把它们连成一串,还在领头舰上插上纸炮,最后才把苧捆拖回家。依然是熟悉的巷子,门口还是黄杨与月月红。忻若姐弟三人同他们祖母围坐在葡萄架下“做苧”,拿着苧刀、右手的大拇指戴着笋壳帽,像摸像样地“做”着。忻若好像没有睡醒,心不在焉地剥着苧皮,活没有干出多少,却把手划破了,疼得她直哭,哭醒之后反而笑了。“亓山河,我又梦见你了!”忻若兴奋地说。
亓山河早已干枯,成为一条臭水沟,还堆积了很多垃圾,只有在梦里忻若才能见到往日那如歌、如诗、如画的亓山河。忻若也只能在梦里追寻它——亓山河,还有它的守望者亓山及塔,那里有她祖辈们的气息,有她童年的梦迹。
(注:本文节选自陈迦南著作《梦影》,福音时报蒙作者允许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