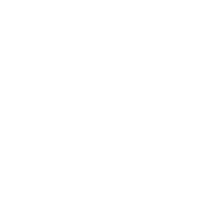那个加略人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圆就把夫子卖了......
忻若把她家“鹌可”叫做犹大,因为他很像那个加略人犹大。
“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风流不可阻挡......”,忻若的舅舅神气地唱着。忻若看到她爷爷瞪了鹌可一眼。“爹亲,娘亲不如……亲;千好万好不如……好。”,小伙子看着老父亲摇头晃脑地又唱起来,唱完了又狠狠地说:“阿哥、阿姐都是反革命,我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他说得声音大大的,边说边走,又唱起歌上他的班去了。“什么反革命?不就是信上帝吗?政府都没有定罪名呢!他倒是在门口乱喊,人家还以为真的是反革命呢!这个犹大!”,忻若气愤地说。“阿哥、阿姐”就是忻若的父母。“阿哥”是老夫人的儿子,是鹌可的姐夫与异父异母哥哥。
老先生把有龙图案的古董收起来,刚刚藏好,戴红袖章的中学生们就来了,“我们是红卫兵,有人说这里问题很严重。”,一个高大的头头站出来说。
“哦,红卫兵同志,早啊!请坐,你们辛苦了,可是昨天来过红卫兵了,他们看了户口本说我们成分好,不用搜查......”,老夫人不解地说。
这次来的红卫兵都是中学生,比头一天的高大,这一大班人马就是犹大叫来的。亓街就有红卫兵指挥部,有人亲眼看到忻若的舅舅去叫他们。说:“这个家问题很大,你们要好好抄一抄。”,所以这批大的一来就准备长驻的。他们一来就乱摔乱打,后堂满地都是碎玻璃、画框、揉成一团的画、瓷片、珊瑚块。“我觉得这个南瓜有问题!”一个满眼闪着疯狂寒光的红卫兵说着就拿起锤子向摆在地面椅子边那个最大的一个南瓜砸去。“这就是‘天荒凉,地悲哀’的日子吧!连地都要受蹂躏,地也有问题吗?。”,看着远处那些在橘园里挖地的红卫兵,忻若摇摇头,不堪设想地说。“你们,红卫兵是狗生的。”一个叫谷声的邻居小男孩小声地朝橘园里的红卫兵骂了一句。“只有你,谷声才有正义感。”,忻若心里说。忻若觉得这句骂人的话用在这些疯狂的红卫兵身上还挺合适,尽管很俗,很难听。
“毒药!毒药!搜出毒药了!”,一个红卫兵举着一个小瓶子说。瓶底里有一团紫光闪闪的粉末。“是啊!这就是授(后)娘要毒授儿(继子)用的。”,一个邻居老太太作伪证说。“拿去化验!拿到实验室去!”,头头下命令说。邻居们从门口一直站到街上,睁大眼睛,伸着脖子看热闹。
去化验的兵仔下午就拿着药瓶回来了,“是一般的消炎药粉。”,那小子对头头和老夫人轻轻淡淡地说。
老夫人点点头,没说什么。
“你们三个饿吗?老夫人对忻若姐弟们说。“我们都饿得不知道饿了!”,姐弟们说。“最好能洗洗脸!”,忻若自言自语地、失神地看着邻居家那闪烁着夏日白光的屋顶说。“是啊,都第六天了,他们还没有要走呢!”,老夫人对孩子们轻轻地说。红卫兵们日夜轮班驻扎着、不停地看守着,他们每次换班出去都把老先生的画或艺术品偷偷地带出去。“简直是一群小偷!”,忻若真想冲他们喊贼,可动动嘴,想说又忍了。
“你们家为什么没有宝像和红宝书?那你们怎么早请示,晚汇报?”,那个红卫兵头头高高在上地、教训人似地责问着。“买!买!买!一定买!立刻买一张!”,老夫人微笑着、恭敬地说。“去合作社买一张侧面的来!”,老太太对忻若的姐姐说。合作社就在亓街上,十多分钟之后“宝像”就买来挂在上间的板壁上,那是一张毛主席坐在桌旁写字的图片。忻若想起:“当敬拜主,你的上帝!”那句话。“我知道为什么娘娘说买‘侧面’的。”,忻若想着,暗笑一下。
圣经、赞美诗和其他书都被装在箩筐里,一筐一筐地摆着,这是抄家的第七天。红卫兵们似乎显得仁慈了一点,午后全家人吃七天以来第三顿饭,一点泡饭和咸菜。
这一天红卫兵都在忙活着,进进出出地,“怎么回事了?”,家人们猜测着。一筐筐书被抬到后堂的门外,天渐渐暗下去,一张圆凳子也被搬到外面,书从筐里拿出来,堆在地上。
天全黑了,忻若在玻璃门内往外看,一堆大火烧起来,火光冲天。书一本本被撕开,被抛到火堆里。忻若看到那个红卫兵头头站在圆凳上宣读犹大写的那一大打控诉词,院子和半条胡同都站满了邻居、红卫兵及过路人,人们静静地听着、看着。控诉词读了好久好久,时间一分一秒、一点一丝慢吞吞地磨蹭过去,全家人都聚在后堂的玻璃门内,看着、听着。“最后让我们振臂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岁,万......”,听到这里总算完了。“哼,这个犹大!手颠得比红卫鬼们还起劲,把你的手臂‘振’断了,把你的嗓子‘呼’哑了才好!全家人都被你一个犹大出卖了!”,忻若看着玻璃外面那满面笑容、得意扬扬的舅舅痛恨地说。
“你这‘犹大’我们家的败类!怪不得你能进这样的工厂工作。”,忻若愤愤地看着门外的舅舅说。“不就是为每月三十元的工资吗?你竟把全家人都出卖了,就像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圆出卖耶稣一样。”,欣若心里很难过,为这个家,特别是为爷爷有这样一个像犹大的儿子难过。
“多么奇怪啊,像‘犹大’一样,舅舅他总是与数字‘三十’联系在一起,他一至四岁的时候被送到他舅舅家里寄养,爷爷每月为他支付三十银圆。如今在他三十岁时他有这一份用出卖家人换来的工作,而这份工作的工资刚好也是三十元。”,忻若不解地想着。从那时起忻若就把她舅舅叫做犹大。
犹大搬出去了,这个家和橘园显得平静多了。可是老先生心里难过,他觉得没面子,因为犹大搬到一个老妇人家里去住。那妇人看起来可以做犹大的妈,而且她有过两任丈夫,原先说要把女儿嫁给犹大,结果他们自己“合铺”了。
“断子绝孙啊!”,禇老先生愤愤不平地说。“还有这没完没了的烟......”,老先生看着隔河对面那个大烟囱自言自语地说。那是犹大工作的地方,那里废气、有害气体日夜不断。一阵风把废气刮过来,橘园里橘树、无花果、葡萄、蔬菜及其他植物都遭灾,掉果子、掉花、掉叶、枯株,留下的树叶或菜叶子,大部分像被火烧过,半枯的、焦黄的。那个工厂还排出废水,使沿街那条美丽的小河变成了臭水沟。人们诅咒大烟囱,痛骂犹大所在的工厂。
橘园的篱笆总是被邻居弄坏,特别是水井边以及通往水井的小路边,那里对着每一家的小门,他们是想让他们家的小鸡进橘园吃草、吃虫子。小忻若不得不常常要修篱笆,修篱笆、拔杂草成为十来岁欣若的工作,她也施肥,在橘园里她从早忙到天黑,什么都做。橘子虽然结得少了,可年年总能收一坛半缸的,这一家人的日子又在期盼、祈愿、希望里熬着。
忻若姐弟们都没有去学校上学,可他们早就识字、读书,晚上是忻若读书的时候,大抄家之后,家里几乎没有书可读了,可老先生房间的一张小桌的屉斗里总有可读的东西。那里是放马桶的地方,门拉过去就是一个隐蔽的方便处,而这些读物是爷爷找来给他自己当手纸用的废纸,有课本残页,有毛选片段,也有革命故事,缺页的小人书等等,这些“读物”也就成为“方便书”,因为“方便”的时候总要翻翻、看看,顺便把平整一点的拣出来作为“夜读”材料。除了这些“读物”还有满街的大字报可读,出门走几步就可以读到。忻若一家人还有一本圣经可读,那是禇师母藏起来没有被抄去的“孤本”。
一到秋后忻若一家人必须防台风,楼阁儿里那些凹塌下来的瓦椽都用粗竹竿支撑着,陋雨的地方放着盆盆罐罐接水。台风一来房子就摇晃起来,损失最厉害的是橘园里那一大片葡萄架,半天或一夜之间全倒了。台风一次次来,一年要来好几次,葡萄架倒了又修,修了又倒,每倒一次,埋在地里的那一段竹柱子就要断在土里,而柱子还是那几根。忻若经常跟她爷爷一起修葡萄架,看着一年一年矮下去的葡萄架,看到要倒似的自家房子,她心里很难过。
忻若觉得还有一种“台风”更可怕,那是一种来之前有“先声”的那种“别样的台风”,就像人们听到“狼来了!狼来了!”,一听到风声就丧胆一样,可真正来的时候却是悄悄的、有针对性的突然“袭击”。这样的“台风”是一种疯狂的“革命行动”,是一群负有“光荣使命”的暴徒对无辜者的袭击。这样的暴徒组织叫做“工宣队”,这是继红卫兵之后的第二代产物,而他们的行动就叫“台风”。
工宣队一来就翻箱倒柜,忻若躲在一边连气都不敢出,有时工宣队还要把她奶奶叫去盘问。一听到要刮台风忻若总怕得打哆嗦,她会把东西收一收,该藏的藏起来,该烧的赶紧烧,特别是信件,她认为信件会惹出很多麻烦、还会连累别人。偏偏有一天欣若独自在家,当好心的邻居对她耳语说:“这日黄昏刮台风!真的!我悄悄听到的,我家......就在工宣队。”
“不好了,二姊那锁起来的抽屉一定会出问题!其又不在,等其回来就晚了。”,想到这里,忻若就把她姐姐的抽屉弄开,把里面几封信全烧了。可那晚什么“风”也没有来,却把朋友寄给她姐姐的信全烧了。“那些里面有我多年来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零碎钱呢!”,直到几十年后她才听她姐姐说起这事。
“你应该认清你的阶级,你的历史,不要相信上帝,要相信我们;如同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和马克思主义,规劝你的儿子、儿媳妇不要信上帝,那样他们就可以立刻回来。”,在工宣队司令部,一个工宣队员滔滔不绝地对禇老夫人说。“还有,你有两个孙女,让大的上山下乡去!”,那家伙又接着说。
“好!好!让她‘回原籍’去。”,老夫人恭敬地说。
老夫人叫忻若的姐姐去乡下看望亲戚,避避“风头”。回来时“上山下乡”的矛头已指向学生,即所谓的“三届生”。亓街上有不少自愿报名的,他们都去边疆。有不响应的,马上有“锣鼓队”进驻这一家,除了有人日夜在他们家里闹之外,这家的家长必须在门口敲鼓,一边敲一边喊“我破坏支边!我破坏支边!”直到支撑不住了,乖乖地让自家孩子去报名。
去边疆“修地球的”走了一批又一批,工宣队转为造反派,造反派又分作两派,少数的与政府官员们组成叫做总联的保皇派,多数的就是工联。两派开始打起来,起先用棍棒,后来竟动起枪支了。人们除了住在市中心危险地段需要逃难之外却活得无拘无束,只是有点困惑。忻若和家人倒觉得轻松了许多,他们家和整个橘园还成为朋友家的避难所。
偶尔听到枪声,一听到枪声人们就钻到铺着棉被的桌子底下。“闹派”的工厂都关门打仗去了,犹大所在的工厂也不天天排废气了,橘园又茂盛起来,南瓜大丰收,橘子又多起来。无花果是连废气也不怕的,这时长得更加喜人,可是被偷得更凶。邻里们个个喜欢无花果,十多岁的大孩子们在苎园的上方亓山腰底搭建了两个碉堡作为偷无花果用。偷无花果的时候他们也顺便偷橘子或别的什么,于是看守无花果成为忻若姐弟们繁重的任务,甚至夜里他们还要在橘园里守着。
“上帝开恩啊!让我看到您的仆人、我们受苦受难的儿女,拯救他们吧!”,禇先生坐在屋边亭的小桌边自言自语,一边修补被红卫兵毁坏的一副《故宫》油画。谷声和忻若姐弟在旁边看着,他们看老先生一点一点地挤油彩,一笔一划地修补那些圆柱子、梅花、雪地上的花瓣和觅食的小灰鸽。小桌上还摆着贝壳、旧瓦罐、水泥糊糊,“爷爷,这是作什么用的?阿爷,这是什么?”,几个孩子好奇地问着。“这就是假山上的宝塔,那个大的贝壳可以用作小亭子的顶盖。”,老先生笑着一面比画一面耐心地给他们讲解。
“褚先生,我要一对水泡眼,我要一对黑花背,我要有花点的......”,邻家男孩女孩们走进来,他们手里举着玻璃罐头瓶子、汤盆子、大饭碗围在鱼缸旁边要买小金鱼。老先生用纱布捞子一对一对地捞给他们。
养金鱼成为褚先生新的爱好,每天早上老先生都去小河边捞一种叫做虾耔的小生物给金鱼吃。早饭后他又出去为橘树找肥料,炉灰或水沟边的肥土,其中也会有些可卖的橘皮或破布之类的废品。“好可怜啊,爷爷!为了能买些他喜欢的花花草草的,要积攒这些东西。”,忻若看着有些微驼的爷爷的背影这么想着。
忻若早上起得很早,她爷爷喜欢什么,她也喜欢什么,可有一天早上她发现她爷爷把一小坛金鱼都倒在茅坑里。“我再也不养你们了!”,忻若看到她爷爷一边倒一边愤怒地说。看到一大缸的金鱼一夜之间不见半条踪影,忻若才知道怎么回事,“全被偷光了?这么好的金鱼!”,忻若又心疼又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等我长大,有了我自己的家,您就同我一起住吧,我一定要给您很多钱买漂亮的植物或买更多的金鱼。”,忻若同情地喃喃自语着。
犹大想搬回来,他叫朋友来向他父亲禇先生说情,“......您要心里有准备,如果那“狐狸精”来吵来闹,你们每一位都要狠狠地对付她,把她赶走,然后我小姨子准备嫁给他。”,犹大的朋友严肃地说。
禇先生心里很难过了,他怕一闹腾更加没面子了,他整天琢磨着不知怎么办,夜里也睡不着,东西吃进去都消化不了。而在这一、二天里那老妇也出马了,她没有来闹,却作为关心犹大的亲戚去找那位朋友,与其“共同谋划”,“同商大事”,于是全盘“计划”都被套出来,结果是犹大被抓得更紧。
禇先生第三天晚上就去世了,他看起来像睡着一样,他的面容显得和蔼、平静,忻若想起一首赞美诗:靠主而睡,实在享福......“爷爷您睡得很幸福很平静,脸上还带着希望的笑意。您一定是梦见我父母,也就是您的女儿女婿,他们都平安回来,就像‘歌唱来到锡安’那样地快乐。我们大家还一起美美地吃着您在自家橘园里培育出来的、金灿灿的大橘子.....”,忻若说得泪流满面。
在老先生的葬礼上家人和教友们放胆唱赞美诗,做祷告。送葬的人很多,其中有谷声全家,谷声还作为他家的代表把老爷爷送到墓地。“爷爷您放心安息吧!我们会看好橘园,还有您喜爱的那些‘花’”,下山时忻若转身望着坟墓对她爷爷又说一句。
在回来的路上忻若想了很多与犹大有关的事,犹大的霸道,犹大的虚伪,犹大的结局。忻若也想她爷爷的一生,爷爷工作过的地方,还有橘园里的爷爷。想到再也见不到爷爷,忻若心里很难过,想到爷爷是被犹大气死的,她更加气愤......
(注:本文节选自陈迦南著作《梦影》,福音时报蒙作者允许刊登)